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7月

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
在前後一年多的時間,作者走遍了縣境內的許多村莊,尋找和觸摸那些存在與過往,與數不清的人在曾經的碾道邊或水井旁,在田壟上或場院里,交流和探討那些屬于鄉村文化範疇的元素和符號。只能說,那是一口愈挖愈清涼甘甜的水井,它甚至有一種魔力,吸引人從一走到十,從十走到百。 我從十幾年前的一個黃昏開始迷戀鄉村。鄉村是人群聚集的地方,祖祖輩輩都在這里生息繁衍,傳說繁密得像天上的星星。 我在日落黃昏的大堤上聞到了鄉村的味道,是從聲音引起的。鄰居家養的牛母子在這個黃昏經歷了生離死別,小牛被人牽走了。母牛從那個黃昏開始號啕,一聲接一聲地,一聲比一聲淒慘地,哭。雖然已經過去了十幾年,我只要想到那頭牛,眼眶還是濕的。 牛哭了三天三夜,我三天三夜沒有睡好。我發現那種味道會從房屋、樹木、人群、家畜、農具、糧倉里溢出來。味道有些古舊,有些殘破,可卻讓我迷戀。我在思考我迷戀的是什麼,很久以後我給了自己答案︰我迷戀一個叫鄉村的地方。 那個時候我喜歡一個人到很遠的地里干活,累了就坐在地邊田壟上,天馬行空地想很多事。天地廣闊無垠,田野碧綠有聲,可我的心卻像干渴的禾苗一樣卷曲著,不知如何讓她舒展。 鄉村在我的感覺里很重要,可我不知道拿她怎麼辦。 我不能把她像只隻果一樣裝進兜里。不能把她像盤縫紉機一樣帶進城市。而且,她也不可能變成一份嫁妝……我所能做的,也許只是為她寫一本書……所以許多年後,我仍需要走出城市去看她。開始是生我養我的地方,後來我發現任何一座鄉村都可以慰藉我。最老的一棵樹,或者廢棄的一口水井。這里與那里沒有什麼不同。狗看到生人都要狂吠,天空飛翔的鳥有著相同的名字。樹下坐著的老人都有相似的面孔。他們恬淡地述說著時光和歲月,為一場春雨或一場瑞雪咧著沒有門牙的嘴。 鄉村是什麼?是母親。是根。是精神。是靈魂。還是愛人。 尹學芸,1964年生于天津市薊縣。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已發表各類文學作品200余萬字。主要作品有《難得浪漫》《女人是禍水》等。現為天津市作家協會文學院簽約作家。
開圈 新宿 看青 場頭 打 兒 掄火球 出河工 扎王八 翻坑 爬瓜 打頭兒 看燕子 推碾子 鋦盆鋦碗 工分 小喇叭 病 打黃狼 燒窯 采菜 車把式 撿麥穗 玩打仗 赤腳醫生 炭火盆 熱炕頭 跳房子 飯瓢兒 汆子 炕席 砸鍋 講古記 開襠褲 姑姑鞋 盤纏 上馬子 打夾紙 踩垛 蓋頂 梢門 �笆籬 豆床 跟腳兒 過廟 打尖 雞蛋頭 搬工 土牛 風箱 加工廠 彩禮 干親 豬胰子 桑木扁擔 念喜 撿糞 六奶奶 相好 針線板 地盆子 柴雞蛋 砸坷垃 打夯 洋取燈 鐵板大鼓 手扶拖拉機 玻璃錘兒 貼餅子熬小魚 白汗兒 手推車 屎瓜兒 趕拉軌子與哈巴狗子 黏火燒 猜撞客 自留地 渡口 跑冰 毽兒燈 鬼剃頭 散轉兒 杠頭 輪官馬 摸河底 四合一 交公糧 夜戰 薅苗 彈弓 刨白薯 抄藤子 姆 平整地形 八碟八碗 壓箱底 蒺藜狗子 打韌頭 合作社 表演唱 捋榆錢 貧下中農
家鄉被一條河流三面環繞,在平原和窪區的交匯處,有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 兒時的記憶經典凸顯在某一種狀態下,似光那樣侵襲,而又似霧那樣模糊。走在村莊里,經常有某一種觸動像琴弦一樣能發出響聲,那是對故去的一些人、一些事、一些場景、一些有形或無形的東西的懷念。那種懷念是尖銳而又綿厚的,帶著長長的哨音。那些已經消失的,或正要消失的,或遲早都要消失的詞語,其實不單是詞語,而是它們涵蓋的事物本身,不經意間,都在地勢長河里湮沒了。在虛妄里,我甚至覺得它們應該走入輪回。只是,我們看不到這種輪回的復生。它像塵埃一樣在歲月的經輪里旋轉,誰都看不到它,但它們自己能看到自己。 于是我萌發了寫《慢慢消失的鄉村詞語》的想法。開始只是三篇、五篇,因為給報紙寫專欄的關系,湊七篇都難( 報紙每次連續發七篇)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種無窮無盡,而這種無窮無盡恰是鄉村智慧的賜予。在前後一年多的時間,我走遍了縣境內的許多村莊,尋找和觸摸那些存在與國王。與數不清的人在曾經的碾道邊或水井旁,在田壟上或場院里,交流和探討那些屬于鄉村文化範疇的元素和符號。只能說,那是一口愈挖愈清涼甘甜的水井,它甚至有一種魔力,吸引人從一走到十,從十走到百。 百篇短文即脫胎于此。 許多章節都是信手拈來,即無需籌劃,也不用構思。它就在大腦皮層的某一處沉睡,既有現成的人物,又有現成的故事。可有些遺憾也讓人莫可奈何。比如,我寫到一種棋藝“看燕子”,寫它是因為有故事,好寫。可是,鄉親們在田間地頭玩的棋藝,許多都比看燕子”復雜有趣。我稍稍做了些調查,就有二十余種。我不可能把二十余種棋藝都寫進文章,除非我想編一本棋譜。再比如““打 兒”,類似的游戲還有抽冰猴,還有踢蛋兒,還有玩扎槍。可我覺得那個“ ”字有趣,小大小,相個謎面。平時幾乎用不著那個字,可一旦把它從文字的瀚海中揀出來,它就成了一段令人愉悅的記憶。這,是不是一種神奇呢? 家鄉的方言中,許多口語化的東西是不能用文字準確描述的。有時候,甚至連找代用字都很難。因為那些讀音,漢語拼音根本沒法注釋,且不囊括于四個聲調之中。遇到這種情況,翻康熙字典都沒用,我只能找音或意相近的漢字貼一貼,實在貼不上去,就只能忍痛割愛。而有些方言大概使用地域遼闊,僥幸被收進了新華字典,這讓我有他鄉遇故知的喜悅。 ……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2015年)第三版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2015年)第三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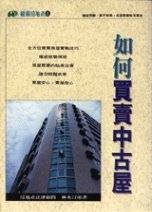 如何買賣中古屋
如何買賣中古屋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2018年)...
土地開發實務作業手冊(2018年)... 第一次買房子就上手(2009年修訂版)
第一次買房子就上手(2009年修訂版) 巴慕達:令人稱奇的設計經營從零到建...
巴慕達:令人稱奇的設計經營從零到建... 1萬元買屋致富
1萬元買屋致富 第一次買房子就上手(2007年修訂版)
第一次買房子就上手(2007年修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