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人依舊披肝膽 入世翻愁損羽毛:劉雨虹訪談錄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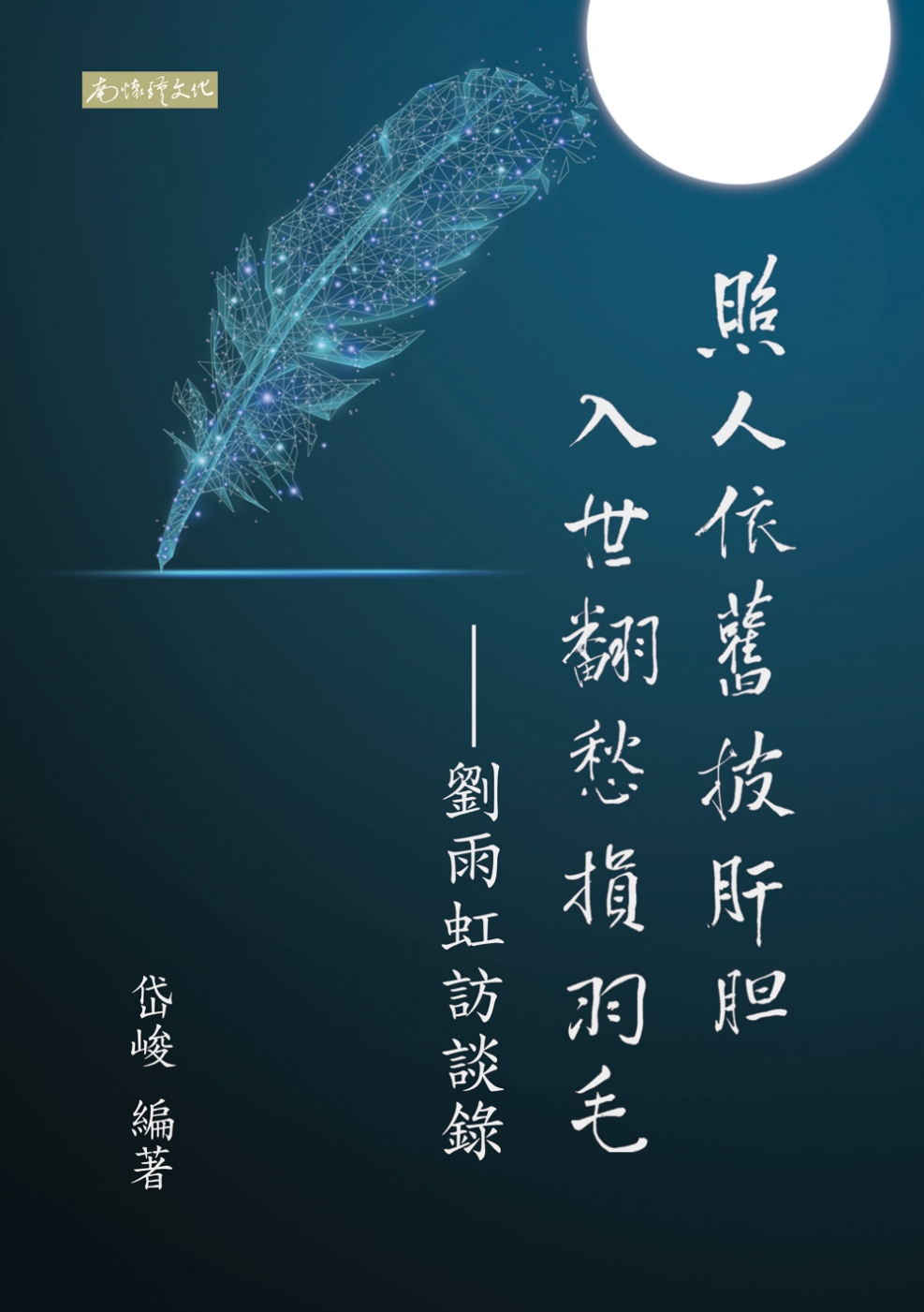
照人依舊披肝膽 入世翻愁損羽毛:劉雨虹訪談錄
聆聽百歲老人講述世紀傳奇──南懷瑾著作最佳代言劉雨虹的人生行路。
◎從家庭背景、學習成長、婚姻交友,到追隨南師,且看奇女子走過一世紀的人生故事。
◎「照人依舊披肝膽,入世翻愁損羽毛」是南師對劉雨虹的評語,是讚賞也是勉勵。
◎作者筆觸生動真誠,雨虹師的人格風範在充滿細節的史料故事中自然流出。
「我覺得一輩子過得太熱鬧了,我自己一生有很多奇遇,我告訴你,我這麼想,現在年紀這麼大,假如我涅槃了,離開這個世間時,請大家為我歌唱。」這種莊周「鼓盆而歌」的生死觀堪作雨虹師一生曠達的總結。
劉雨虹,一九二一年生,已晉百歲嵩壽,追隨南師四十三年,與南師亦師亦友,孺慕情深,南師曾親函四十三封信予劉老師,後編成《懷師的四十三封信》一書。劉老師一生為整理出版南師的著作而勠力不懈,南師仙遊後,並整理出版南師未面世之書籍多種,可見其深得南師思想精髓與信任,南老師視之為「道友」,稱她為自己的「總編輯」,為南師著作的第一代言人。
雨虹師生於西風東漸,傳統文化花果飄零的新文化五四運動時期,經歷過延安、西昌、成都、南京、臺北及美軍顧問團等各處的文化洗禮,卻在知命之年從學南師後轉變想法,進而襄助南師弘揚傳統文化。有心人訪百歲人瑞,留下一部世紀傳奇,其間的思想轉折,讀者們或也能從岱峻先生對雨虹師的細膩挖掘中,窺見一二。
陝北公學、西昌康專、重慶先修、成都金陵,涉險參學數座黌宮;
曉園大姊、瓊瑤姪女、春翔姊夫、夢蝶詩友,有緣情結幾多人傑?
適袁府,蹈過兩次戰火,體證家國命運;
居台島,歷經幾度寒暑,感悟三界悲欣。
追隨南師,編輯濟世良言;
沉潛蘭若,寫出平常心語。
~~人生無奇君莫笑,當我離世,請為我歌。
作者簡介
岱峻
本名陳代俊,畢業於重慶師範大學中文系,執業媒體,定居成都,出版有《發現李莊》、《消失的學術城》、《李濟傳》、《民國衣冠 風雨中研院》、《風過華西壩 戰時教會五大學紀》、《弦誦復驪歌 教會大學學人往事》等著作。
出版說明
編著者言
第一章 緣起華西壩
第二章 故土 親人
第三章 童稚到花季
第四章 去延安
第五章 川康遊學
一 西昌兩載
二 負笈錦城
第六章 從南京到臺北
第七章 先生與女兒
第八章 袁家那河水
一 袁曉園的故事
二 袁行恕、陳致平與瓊瑤
第九章 沒有文人 世上會多無聊
一 大姊雪琴 姊夫春翔
二 好友周夢蝶
第十章 我是南師永遠的義工
第十一章 搞了半天 還是凡人
編著者言
岱峻
這部訪談錄,初擬兩個書名,一為現名,另一為《當我離世時,請為我唱歌》,都其來有自。後者,劉雨虹老師在回答馬宏達的訪談時說:「我覺得一輩子過得太熱鬧了,我自己一生有很多奇遇,雖然不發財,也從來沒有受過窮,好像一切都很順吧。我告訴你,我這麼想,現在年紀這麼大,假如我涅槃了,離開這個世間時,請大家為我歌唱。」我很讚賞莊周這種「鼓盆而歌」的生死觀,以為堪作雨虹師一生曠達的總結。
雨虹師在回覆我的親筆信中寫道:「題目仍用『照人依舊披肝膽,入世翻愁損羽毛』吧,那是南師對我的評語。」於是,我試圖去找尋這段「公案」的原委。雨虹師在《禪門內外――南懷瑾先生側記》一書中寫道:
有一天,記得是一九九六之秋,老師(註1)提早來到會客室,進門就囑親證師鋪設筆硯紙張,原來要寫字了。
我站在一旁觀看,第一幅老師寫出幾個大字:
照人依舊披肝膽
入世翻愁損羽毛
再看下去,原來題款是寫給我的,一時不禁吃了一驚。我並未向老師求字啊!現在為什麼先寫一幅給我呢?大概是因為我站在旁邊,算是順水人情吧。
老師繼續寫下去,寫了不少幅,字也越寫越好。我站在旁邊不自覺的喊起好來。
老師的字自成一派,但每幅都似有敗筆。奇怪的是,這並無損於整體的自在逍遙的氣勢。就像鑒賞詩的人所說:「無好句有好篇」,每句詩雖很平凡,但整篇讀下來卻引人入勝,毫不平凡。
另有些詩是「有好句無好篇」,每句都是金句,但通篇讀下來,卻不知所云。
老師的字是「有好篇」之類的,別人想學也學不來,雖有敗筆,整幅看起來風格獨特,有仙風道骨之感。
寫到最後一幅,也是給我的,可能是回應我說「越寫越好」的那句話,這一幅敗筆少,是古人的詩句。
但使我越想越納悶的,還是那句「入世翻愁損羽毛」的話,總覺得有些玄機。當天夜晚似乎半睡半醒,腦海中總在若隱若現的飄浮著這句話。
愛惜羽毛是做人的基本常情,正人君子都會愛惜羽毛,但在老師的口氣裡,愛惜羽毛似乎成了一種障礙。
在胡思亂想理不出頭緒時,忽然想到不久前與老師的一段對話,那天在說到《人文世界》復刊的事(一九九六初),我好像說了一句「不能丟人」之類的話,老師卻說:「我不怕丟人。」我又說:「老師不怕丟人,但是我怕丟人啊!」
這也是愛惜羽毛的意思,做事不能丟人現眼,不能被人笑話……
又想到有一次,說到任事不易,被人批評,老師立刻說:「要做事就不能怕被批評。因為只要做事就會遭人批評,做得不好有人罵,做得好也有人罵,怕人罵就不能做事。」
對啊!仔細回想一下,老師是不管別人的批評或背後謾罵的,他一概置之不理。前面我也提到過,對他人的閒言閒語,他會說「人家要吃飯嘛!我們也要吃飯嘛!」
第二天又見到老師時,我說:「昨晚參了一夜的話頭,今天悟到了,愛惜羽毛是我的習慣,有時為了自己的羽毛,不肯去做該做的事……」老師沒有任何答覆。――這段「公案」,蘊何禪機?
雨虹師是一九二一年生人,已晉百歲,耳尚聰目略明,口齒清晰,思維縝密,表達精準,讀書寫作,至今不輟。
雨虹師身世非凡,三姐弟皆學有所成,姐夫趙春翔,是享譽世界的大畫家;先生袁行知乃江蘇武進名門,曾任聯合國糧農組織專家;堂兄妹袁行霈(北大教授、古典文學家)、袁行恕(女作家瓊瑤之母)、袁曉園(中國第一女外交家)等,滿園芳菲。
雨虹師也一生傳奇:抗戰前讀到高一,受王實味等老師及左翼同學影響,棄開封女中而讀中共栒邑陝北公學分校。後轉延安本校,毛澤東曾與她意外握手。一個生性自由、顧惜羽毛的知性少女,因患牙疾,從此離開那片紅色的土地;輾轉到達四川,犯險過夷區到西昌,就讀邛海邊上的國立西康技藝專科學校;後到成都,結婚生女,插讀四川大學蠶絲系及金陵大學園藝系;抗戰勝利到南京始完成學業。一九四八年底,搭乘陳誠接陳老夫人便機入臺,先後任華僑通訊社記者,美軍顧問團翻譯十數年。一九六九年,追隨「縱橫十萬里,經綸三大教」的南懷瑾先生,參與籌創《人文世界》雜誌和老古出版社,擔任總編輯,記錄整理出版南老師的大部分著作。南老師視之為「道友」,稱為自己的「總編輯」。兩者關係「亦師亦友」、「半師半友」。雨虹師除了編著《懷師――我們的南老師》《我是怎樣學起佛來》,將記錄南師禪七吉光片羽的《習禪錄影》部分內容譯為英文(書名《Grass Mountain》)外,近年亦編輯了《雲深不知處》《南師所講呼吸法門精要》,陸續出版自己撰寫的《禪門內外――南懷瑾先生側記》《袁曉園的故事》《東拉西扯:說老人、說老師、說老話》《禪海蠡測語譯》《懷師的四十八本書》等著作。
我與雨虹師相見恨晚,而一相識即儼然百年。拙作《風過華西壩》經科學家朱清時院士推薦給雨虹師。老人讀過,打來電話交流,遂有了面晤之緣。二○二○年七月十日,我們乘坐高鐵到了太湖之濱的淨名蘭若,次日恭逢雨虹師百年壽宴,聆聽老人講述百年傳奇,遂存心完成一部口述史,於是記錄整理出這些文字。
成住壞空,乃佛教對於世界生滅變化之基本觀點。宋代釋祖欽有偈頌:
「寰中日月,量外乾坤。舉起也千差萬別,放下也不立纖塵。」西哲也認為,人生不過是不斷背包袱和卸包袱的過程。雨虹師生在五月,本該天乾地燥,結果當時下了十八天雨,父親即為她取名雨琴。後來她自己改名雨虹。
也許,這是她的人生期許:烏雲翻滾,雷電交加,暴雨滂沱,而雨後彩虹,滿目山青。
(註1)本書仿史體例,敘述語言免去敬稱。文中所稱」老師「,除有姓氏專指,餘皆為南懷瑾老師。──作者註
第十章 我是南師永遠的義工 岱峻:劉老師,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那一代新女性,但好像也與佛教緣分深? 劉雨虹:對的。有一個人看手相,說我有七世是和尚。 馬宏達:看手相還能看出這個來嗎? 劉雨虹:誰知道真假啊,只是自己覺得跟佛法有緣。為什麼?我住那個地方在三樓,一樓是東北覺光大和尚,他人不住那裡,臺灣有個比丘尼住那裡,給他看管這個地方。結果有一天附近失火了,這個比丘尼不去喊救火隊,就跑到屋子裡咚、咚、咚,趕緊念經。太奇怪了,我就下樓去問她,她也不理我,只送給我一小本《阿彌陀經》〈大悲咒〉,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些東西啊。我一看那個〈大悲咒〉,一個字都不認識。我說這是什麼玩意啊,我說不行,我非得把它念會不可。我就在那裡每天念,所以我最早會背的就是《大悲咒》,你想我如果前世沒有這個因緣,看也不會看,更不會去背吧。 馬宏達:那時候多大的年紀啊? 劉雨虹:袁保雲一兩歲那個時候,我四十四五歲了(大約是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在家裡沒事,就啃那個〈大悲咒〉。後來就認識臧廣恩,他太太一輩子吃素,是學佛的,是我們老鄉。臧廣恩跟我講,你念觀世音,觀世音會來救你。我說你怎麼知道啊?他說觀音發過願啊。我說人發願不算數啊,今天發,明天不發了就不算了,對不對。社會上人不是就這樣嗎?他說他這個發願怎麼樣怎麼樣…… 馬宏達:《普門品》。 劉雨虹:《普門品》,我不懂啊,《普門品》中說當人臨刑被殺的時候,觀世音來救你,我說觀音為什麼要去救他,他是個壞蛋啊。那時立法委員蕭天石,他要弘揚道家就印《道藏》,在立法委員裡頭預售募款,立法委員大家看面子,就有很多人訂書,他就拿這個錢,把《道藏》印出來。袁行廉(我先生的堂姐)的先生是立法委員,拿到書以後,袁行廉就看,說道家這樣,又是什麼鳴天鼓啊,又是什麼修行啊,看了以後她就過來教我,如何鳴天鼓,我們兩個人就搞這個事。 這個事有興趣最初是袁行廉帶領的,有一個李杏邨,我有一個鄰居湯志平跟他熟。有一次相約去看承天寺廣欽和尚。廣欽和尚只吃香蕉、喝水、不倒單,永遠盤腿打坐。我說奇怪天下還有這個事,就和李杏邨、湯志平,一塊去看廣欽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