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彩青春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4月

無彩青春
矛盾反覆的嫌犯自白、從未出現過的凶器……真相,是這起案子的第三個死者。在真相之後,是賞罰問題,但要在司法裡面找到正義,怎麼會這麼難?
又經過八年的努力與煎熬,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於二○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獲判無罪,全案定讞。最終判決採用李昌鈺博士的現場重建,認為汐止血案現場狹窄,不可能容納四個人同時行兇;全案應是一個兇手、一把兇刀所造成,與蘇建和等三人無關。
與作者張娟芬討論的時候,我們同時想到了法律最矛盾之處:法律只是社會最低限度的保障,但人們總是冀望法律明辨是非善惡。一邊質疑司法的不公,同時卻又深深地依賴法律為我們說清楚誰對誰錯。而夾在這種期望與失望之間的我們,最終會為這樣的落差感到疲倦。究竟我們該將法律擺在什麼樣的位置?這個社會會有包青天嗎?或者,我們需要重新去釐定法律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蘇建和案是張娟芬參與社會運動的轉折點,因為這個案子,她將視野放到了司法改革以及廢除死刑的訴求。二○○四年撰寫《無彩青春》時,張娟芬試圖從堆疊了十多年的卷宗裡,疏理出蘇案的面貌,並潛藏她對於司法制度漏洞的抗議。二○一三年《無彩青春》重新出版,我們則希望將問題拉大一些:可不可以透過蘇案,讓我們用更多元的角度來思考司法?思考死刑?
如果你對死刑還沒有想法,或者你明確支持或反對廢死,都希望可以花一點時間閱讀《無彩青春》。《無彩青春》存在的意義並非勸說人支持廢除死刑,而是告訴我們三位極可能沒有犯下殺人罪的青少年在法庭迷途二十年的故事,這之間他們被判多次死刑,遇見許多人要替他們伸冤,在絕望與懷抱希望之間遊盪、喪失信念後復又得到救援,他們的故事透露出法律的漏洞、司法尚需改進的空間,以及最脆弱的人性。
這個故事裡的警察是否有錯?檢察官是否有錯?承認殺人的蘇建和等三人又有錯嗎?(甚或是有罪嗎?)答案在每人的心中自有定論。我們只是希望透過重現蘇案,能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去思考:法律是什麼?法律及社會有何需要我們推動改進之處?如果讓我們重新思考死刑,我們可以怎麼想?死刑背後所代表的人權,甚或是社會對於人權的觀念,還有可以調整的空間嗎?
在新版序言裡,張娟芬寫到撰寫本書的初衷:「我深受震動,覺得蘇案也應做如是觀:在不正義之中追問更深刻的問題。於是我決定寫《無彩青春》。」
這簡短的句子,正是《無彩青春》一書始終存在的原因:它不僅記錄台灣司法史上的轉捩點,更代表的一個多方面思考的可能。
作者簡介
張娟芬
台大社會系畢業,丹麥阿胡斯大學與德國漢堡大學聯合授與新聞學碩士。雖參與社會運動多年,但在蘇建和案之前,她對於死刑沒有支持亦無反對,深入蘇案後,張娟芬改變了關注司法的角度,重視人權議題,並在撰寫《殺戮的艱難》時決定支持廢死。
她的作品曾獲中國時報十大好書、聯合報年度選書、台灣文學獎。現專職寫作,並準備攻讀博士班,著有《姊妹戲牆》、《愛的自由式》、《無彩青春》、《走進泥巴國》、《殺戮的艱難》等書。
新版序 少年Pi的奇幻漂流第一章 跳過他自己第二章 惡戰的序幕第三章 黑洞隨便說第四章 證據不說話第五章 我所言庭上不相信第六章 看破看不破第七章 蘇爸的消逝第八章 夢幻隊伍第九章 包青天與王迎先第十章 枯萎的記憶第十一章 自白的魔咒第十二章 隧道症候群第十三章 青春降靈會第十四章 如果、如果、如果第十五章 法醫沒聽懂第十六章 扮豬吃老虎第十七章 法官排行榜第十八章 唯一做錯的事第十九章 乾澀的淚眼第二十章 霧中風景第二十一章 深山水遠後記
附錄 蘇案大事記
新版序
少年Pi的奇幻漂流
就像甘藍菜被反覆加熱端上餐桌, 凡人在無盡的重複裡受盡了折磨。 --羅馬作家朱凡諾(Juvenal)
1
第一次被判死刑的時候,莊林勳十九歲。他說,「哪有可能!」那是年輕受冤的憤憤不平。
第一次被判無罪的時候,莊林勳三十一歲。他想:「哪有可能?」那是飽受折磨以後,微近中年的不敢相信。
從十九歲到三十一歲,莊林勳、蘇建和、劉秉郎坐了十二年牢。初解嚴的台灣,大家一方面認為沒有了戒嚴,社會會亂,所以要治亂世用重典;另一方面認為戒嚴已經過去了,不會再有冤假錯案了,所以作奸犯科被判死刑的,都應該殺。
他們三人背負的罪名是殺人、強盜、強姦,正是大家認為該殺的那幾類。於是他們認真寫了遺書,清空牢房裡的東西,準備了「上路」的衣服。他們列名死囚名單長達五年,時時驚險,最後居然生還,簡直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
他們三人的共同履歷如下:
2
蘇案是很多人關心司法改革的起點,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一九九九年,顧玉珍在當台權會祕書長,為了喚起更多人對蘇案的注意與瞭解,辦了「作家探監」活動。回來以後,我寫了〈飛入尋常百姓家〉:
時差。九五年就三審定讞了的三名死刑犯,拖著金屬沉重的撞擊聲來到了九九年。去土城探監兩次,眼前是三條隨時可以被取消的人命,三個早已被宣告應該消逝的形體。槍聲都響過了,我聞到火藥擊發的煙硝味,子彈劃過空氣嘶嘶飛行,慢動作。時間是借來的,卻不知道到底借到了多少。拿一把尺,循著子彈行進的方向往前畫虛線,單薄的胸膛跳動的心就在不遠處。虛線中的空白串起成為實線的時候,三個生命就將斷裂成為虛空。
那好像不是活著,而是暫時還沒死。那好像不是生命,而是類死亡,類鬼魂。搶在某種時差裡,我們會面,進行幽冥兩隔的交談。
當蒼白的面容與我相對,我很自然的去尋找他們與我的關連性。我們年齡相近,他們小我兩歲。被捕的時候才十八、九歲,如果沒有冤案的發生,我們不會相見,彼此的生命也不會因此感到缺憾可惜。如今我們還是在冤案的前提下相見了,無法忽視這個前提,卻很想忽視。第一次見面,我一點都不想問案情,獄中八年,他們說過上千次吧,生命不該只剩下這個。只想若無其事說一點有的沒有的,運氣好的話,也許可以不動聲色的,悄悄收藏一枚微笑。
回來以後的幾天,看了台權會寄來的資料,覺得這真是個政治威權殘留下來的最後冤獄,經典的。營救行動卻盡其所能的匯聚了法界專業人士、社會運動者與「社會名流」,就一個社會事件的行銷而言,差不多也是經典了。台權會的朋友問一位參與營救的法界人士:「您覺得我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沒有!」很難反駁。縱然不想承認。
於是我每天傍晚爬到陽台上高高蹲踞,看著天色的變化直到夜晚正式來臨,山間有時靜默,有時呼嘯,我希望自己強壯,能夠平靜柔和,什麼都不計較。悲沉的心念有這樣的人間美景安慰著,很夠了,很奢侈了。傍晚是一天中令我明確感到外在世界存在的時刻,天光遞移的韻律外於你我意志,外於人世紅塵,「和諧、美麗、敏感、優雅」。山間晶瑩的亮著燈火,那麼謙和節制,天色尚明時一燈如豆,夜色深重時也一燈如豆。很夠了,足以令我善良的微笑。
或許因為這樣,我開始想忘記他們。第二次探監,帶了一些怪里怪氣的書去給他們看,仍然感覺到自己很想忽視那迫在胸前的死亡,獄中八年了,判死刑四年了,這樣一個人會不會逐漸習慣自己鬼魂一般的存在?我幻想跳過一條河,直接來到他們獲得重生的日子,看見他們以清白之身成為社會新鮮人,我為那樣的他們挑選著書籍。當他們又拖著沉重的鐐銬走進會客室的時候,我假裝一切都已完成,時差被消泯了,子彈被收回了,河被跳過了,我假裝天地靜好,大家身輕如燕,嘻皮笑臉。
一轉身走開,我就忘記了他們,只看見魂飛魄散的一隻鬼,曾經為社運寫過柔情蜜意的文字,也寫過劍拔弩張的文字,如今靜默無言,啞著。這是另外一重時差,我們失之交臂,沒有在彼此鬥志高昂武功高強之際並肩作戰,所以幽冥兩隔。他們三人其實以各自的方式懷抱著存活的信心,專注的營救自己,冤獄是人生中的歧出,不知道最後會通往哪裡,但旅程中哺餵著對生命的渴望。只有我在河的這一岸遠眺,看著夜幕低垂。
帶著期望幻想這就是最後一眼,以後三人冤情昭雪,世界遼闊起來,生命終於填進了那些原本就該有的,即使俗事多麼無味,情愁多麼無謂,都好。我們終將痛快相忘,因為不必記得,也許素面相見。也許我們在路上擦撞路邊吵架,互相幹譙一番絕塵而去,心底暗暗奇怪這哪裡來的俗辣怎麼有點面熟咧。連那樣都好。所謂人生哪,不過是飛入尋常百姓家。在那裡,時間是自己的,不用借。
再審宣判的那天,我不敢面對現實。我上了公車,司機在聽廣播,講話的是當時的司改會執行長林靜萍。從她的隻字片語,我拼湊猜測著到底是判有罪還是判無罪,一個後知後覺的人,緊張著擔憂著那個已經宣布了的判決。晚上手握著遙控器,一台轉過一台,眼淚終於流下。
那陣子恰好讀了蘇曉康的《離魂歷劫自序》。他在六四之後流亡美國,全家經歷了嚴重車禍。回顧這一切,他自省:「我只有淺薄的公平索求,不懂得不公平是更深刻的問題。」我深受震動,覺得蘇案也應做如是觀:在不正義之中追問更深刻的問題。於是我決定寫《無彩青春》。
3
《無彩青春》於二○○四年出版之後,蘇案的審判還繼續進行,直到二○一二年,終於無罪定讞。其間有幾件事情,值得在這裡更新補充。
蘇案最關鍵的證據,是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所做的現場重建。他的鑑定報告指出,現場牆面血液噴濺完整,可見行兇時沒有人站在旁邊。現場空間狹小,如果有四個人揮刀猛砍,一定會不小心砍傷彼此,因此推斷兇手應該只有一人。李昌鈺推斷可能的行兇動線,與王文孝「一人犯案」的初供,細節完全相符。
蘇案的第一份無罪判決(二○○三年)是一份妥協色彩濃厚的判決。對於三人是否被刑求,判決說不能確定;到底幾個人犯案、幾把兇刀,也不確定。在一團迷霧之中,「罪疑唯輕」,從輕發落罷。就形式上來看,這份判決將死刑案件逆轉改判無罪,堪稱石破天驚。從內容上來看,它採取折衷策略,無助於釐清事實。所以我寫道:「人放出來了,但真相還在坐牢。」
蘇案的第二份無罪判決(二○一○年)有兩個突破。第一是認定蘇建和有被刑求。自白既是刑求所得,當然不具證據能力;這對於日後的冤獄賠償尤其重要。第二是採用李昌鈺的鑑定報告,認為應是一人犯案、一把兇刀。蘇案的第三份無罪判決(二○一二年)也持相同立場,並且更進一步地否定法醫研究所「四人犯案、四把兇刀」的鑑定報告,認為它沒有證據能力。
李昌鈺的鑑定報告,用3D電腦動畫作成短片以後,相當程度的還原了現場。刑事鑑識的門外漢看了動畫也能夠身歷其境,體會到多人犯案之不可能。直到李昌鈺的鑑定報告,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才真正重獲清白。
無罪定讞以後,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向法院提起刑事補償的請求。四千一百七十日的冤枉,應當如何計價?依據《刑事補償法》,每日補償金額最高五千元,例如江國慶案就依五千元計算。結果高等法院裁定補償蘇建和等人每日一千二百元至一千三百元不等,理由是三人當年被羈押的時候學歷不高、收入不豐。
當年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才十九歲,就被國家抓起來、關到牢裡去、安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一關十幾年,當然無法繼續唸書與工作啊!現在國家倒反過來說,你的青春不值這麼多錢。這就好像一個討厭鬼在超級市場裡,拆開一支冰棒就吃起來,店員要求他付帳,他卻說:「我只願意付半價,因為這枝冰棒已經被咬過了。」
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的生命裡,確實留下齒痕。請問,冰棒是誰咬的?
4
蘇案關鍵性地影響了我對死刑的看法。以前只知道司法「應該」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直到蘇案,我才看見司法「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國家的刑罰,只要一不小心,就不是正義。
二十一年來,蘇建和案經歷了兩階段審理,所受待遇截然不同。第一階段是案發的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死刑定讞,依照當年的法庭實務,檢察官從不到庭,法官與檢察官角色模糊難辨,理應中立的裁判者,往往情不自禁下場扮演追訴者的角色,予人「球員兼裁判」之譏。
第二階段是二○○○年開啟再審到二○一二年無罪定讞。這時候蘇案已經是各界矚目的指標性案件,享有司法的最高規格待遇。二○○三年刑事訴訟法大幅修正,更是一個分水嶺。蘇案再審以後,到庭執行公訴職務的檢察官均是一時之選。然而彈指之間,已經有兩位明星級的檢察官官司纏身。
李進誠在蘇案再審時擔任檢察官。他於二○○五年榮升金管會檢查局局長,隨即涉入喧騰一時的「股市禿鷹案」。二審法院認定,李進誠放出對勁永公司不利的消息給聯合報記者高年億,導致勁永股價大跌,李進誠的友人早已放空勁永公司股票,即趁此機會低價回補。李進誠於二○○八年依貪污治罪條例被判九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全案尚在進行。
更一與更二審的公訴檢察官是陳玉珍。特偵組調查發現,陳玉珍檢察官以職務之便向電玩業者索賄兩千多萬,依違背職務收賄罪起訴。收押多時之後,陳玉珍一審時當庭認罪。案件還在進行中。
我常戲稱法庭旁聽是「無聊體驗營」。想像你正在看好萊塢電影的法庭戲,但是是毛片,一刀未剪,冗長、單調、焦點渙散。纏訟多年的案件大多呈現類似的樣貌:重複已經飽和,正義仍然稀薄。
只要有李進誠與陳玉珍在,法庭便稍減無聊,因為他們都頗擅長表演。否則的話,不難發現聽眾眼神呆滯空茫,視線凝結在蘇建和、劉秉郎和莊林勳的後腦勺。最長方形的頭是蘇建和,最正方形的頭是莊林勳,介於兩者之間、比較圓的頭是劉秉郎。
每一次開庭都有類似的疲憊感:這個空間裡有的是不斷重複與互相算計,「正義」的追尋所剩無多。法庭是檢辯雙方法律技術的競技場。最神聖的正義殿堂也無法避免意義的凋零,弔詭的是我們卻非如此不可。
5
立法院旁邊的濟南長老教會,是蘇案救援的一個歷史地點。他們死刑定讞以後,有好幾年的時間,所有救濟途徑輪流碰壁,司法的糾錯機制完全失靈。救援團體決定每日定點繞行,地點就選定這個古樸美麗的紅磚小教堂。聽說有時候小貓兩三隻,淒風苦雨,靜走變成苦行。最後,蘇案如願再審,救援小隊走進台灣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光榮結束二百一十五天的靜走。
約莫十年以後,蘇案又在濟南長老教會辦活動。小小的露天廣場,溫暖的音樂與燈光,竟然來了一百多人。高中生穿著制服來,圍著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上了年紀的老先生坐在板凳上,不離不棄,直到最後。椰子樹高高撐起,在風裡搖曳,沙沙作響。我真希望當年那堅持靜走的兩三隻小貓能夠知道,現在隨便就叫來一百多人了。
救援團體帶著他們三人從最南到最北,最後剪成的短片再怎麼陽春也令我激動,那些路上隨便一句「你就是那個蘇建和喔?加油!」都多麼珍貴。忘記是哪一年,台北捷運初通車,蘇建和他們三個還在牢裡,最大願望是想坐捷運。於是我們帶著他們的人形立牌去坐捷運。我們在捷運上分發文宣,一位乘客接過以後,憤怒的退還:「我才不要拿,你們都替兇手講話!」
曾經,他們不在,他們只是三個紙板。曾經,我們努力解釋,人家也不要聽。現在,蘇建和可以有模有樣的談法律了,有一回收到他的email,署名只簽個「蘇」,我乍看以為那是蘇友辰律師寫來的,細看才知是蘇建和。劉秉郎被問到如果沒有出境的限制要去哪裡玩,他說沒有想去哪裡,「我們三個都一樣,自從出來以後,我們都很想回家。即使只是幾天而已,我很快就覺得,好想回家喔。」莊林勳得努力才能把下垂的嘴角往上揚。救援團體的人說,這一趟從南到北好累,可是帶莊林勳走出來,他改變很多,單單這個部分就值得了。
我知道誰不在:盧正不在,江國慶不在,鄭性澤不在,邱和順不在,徐自強不在……只看蘇建和案,覺得他們三人倒楣到不行;再看別的冤案,會羨慕蘇建和他們三個怎麼那麼幸運。
用過去的記憶比對著現在的進步。那或許就可以滋養自己,不再多問什麼而繼續頑鬥下去。做就是了,看有什麼把戲什麼招數都使出來,就是,頑鬥到底。
每一次重複都有嶄新的意義, 引領你向神靠近一步又一步。 --甘地
第十八章 唯一做錯的事別人是怎麼向你指控我的,我不清楚,但他們口才那麼好,簡直連我都快忘記我是誰了。──蘇格拉底九十一年十二月五日星期四,下午兩點半,蘇案的辯論庭。按照慣例,審判長逐一提示證據,並且問被告對這項證據有什麼意見。距離汐止血案的發生,已經十幾年了,蘇案卷宗汗牛充棟,所以提示證據得費好一番工夫。隔天早上繼續開庭,好不容易把所有證據都提示完畢,便讓告訴代理人代表被害人家屬發言。林憲同律師首先指出,因為王文孝已經槍決,造成再審所能調查的證據有所殘缺。「除非有強烈到足以排除所有的不利證據或補強證據,否則就沒有無罪推定原則之適用。」接下來是楊思勤律師發言,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說:「剛才林憲同律師的發言,對被害人家屬有利的部分我們贊同,但他剛剛說,本案是殘缺的再審,我不贊成。我們不樂意本案再審,但既然依法再審了,就不能說是殘缺的。」楊律師指出,蘇建和等三名被告曾經控告汐止分局警員瀆職,但警察獲得不起訴處分,可見他們的刑求抗辯並不成立。「我們認為這個案件經過四十七位法官的審判,最後終於再審,除非我們在再審程序發現很重要的證據,足以推翻十一年前的事實,否則在十一年後,以發現一個小皮包就來推翻十一年前一個慘絕人寰的案件,我們不以為然。」石宜琳律師認為,蘇建和等人都曾自白犯罪,而王文忠與王文孝的供詞,是本案很重要的補強證據。何況鑑定報告認定有三把兇刀,也駁斥了辯方「一人犯案,一把兇刀」的主張。「儘管我們多麼不贊成『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殺人償命』,但是這個案子兇手的狠毒,非常少見。請合議庭的各位法官不要被被告楚楚可憐的外表給蒙蔽了,也不要受到未參與審判的外界所影響,更不要被辯才無礙的各位辯護人說服。司法的最後一道防線,就仰賴各位法官來維繫了!」審判長宣布證據調查完畢,開始言詞辯論了。先由檢察官論告。整個審判過程裡,大部分的時候檢察官在法庭上並不很積極發言,站起來跟辯方律師針鋒相對的,常常是告訴代理人。如今檢察官要開口說話了,令人格外期待。檢察官首先列舉本案的證據,包括:王文孝的指紋、警棍與小皮包、二十四元硬幣、菜刀,以及吳銘漢的兒子的證詞。檢察官反駁辯方所提出的刑求抗辯與不在場證明。他指出,王文孝並沒有說自己被刑求,所以他說蘇建和等三人是共犯的說詞應該可信;劉秉郎在檢察官偵訊的時候雖然翻供,但也沒有說被刑求。當年與蘇建和關在同一舍房的何先生與黃先生,對於蘇建和的傷勢說法不一,而在一審時曾經有一位游先生為蘇建和出庭作證,可是檢方調取士林看守所的紀錄,卻發現他從未與蘇建和同房。他也指出,蘇建和一直說他不知道崔紀鎮是檢察官,可是這次再審當庭勘驗偵訊錄音帶,卻發現崔檢察官一開始就對他表明身份了,後來蘇建和也兩度喊他「檢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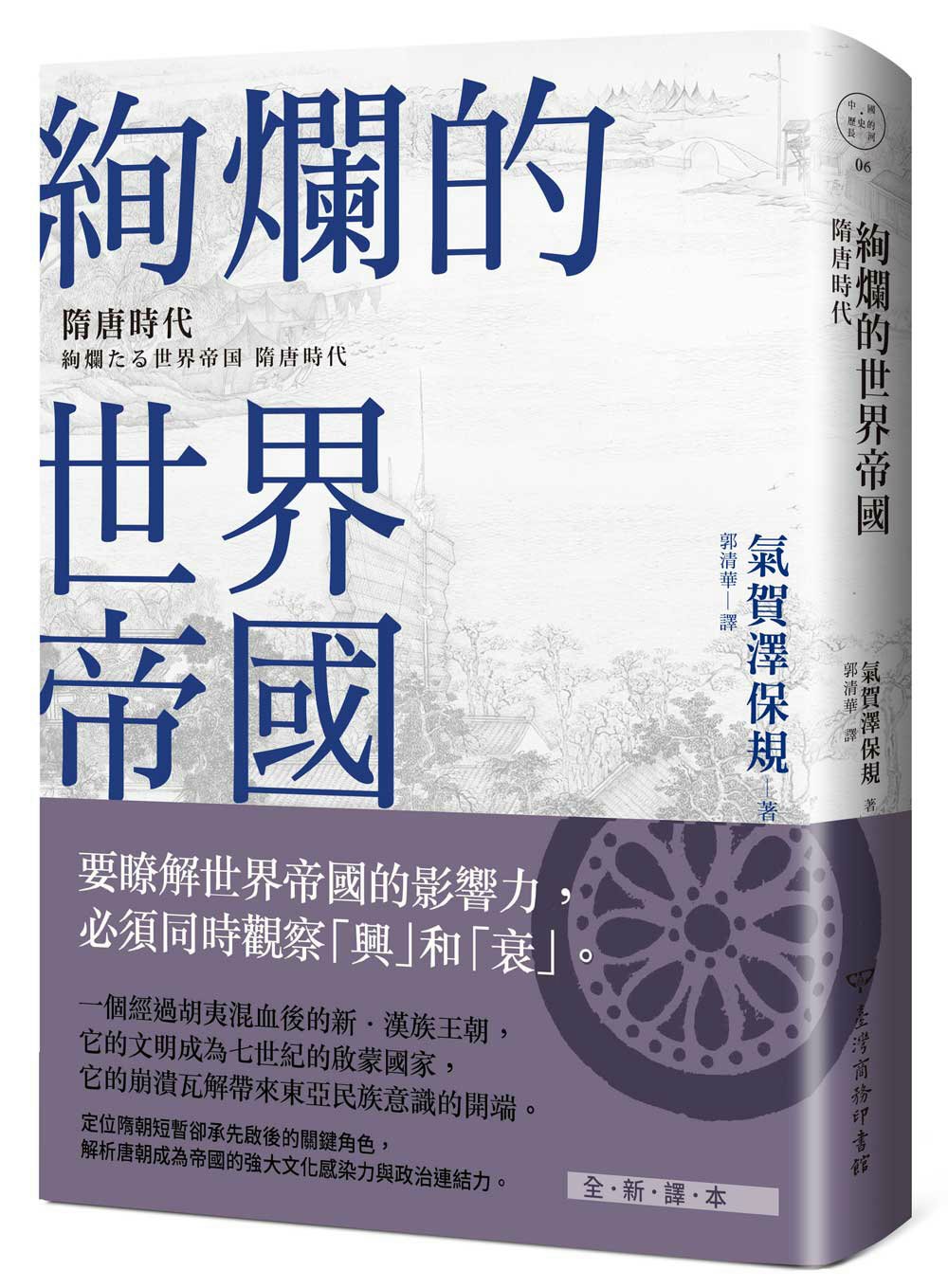 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失去心跳的勇氣:重「心」出發,活出...
失去心跳的勇氣:重「心」出發,活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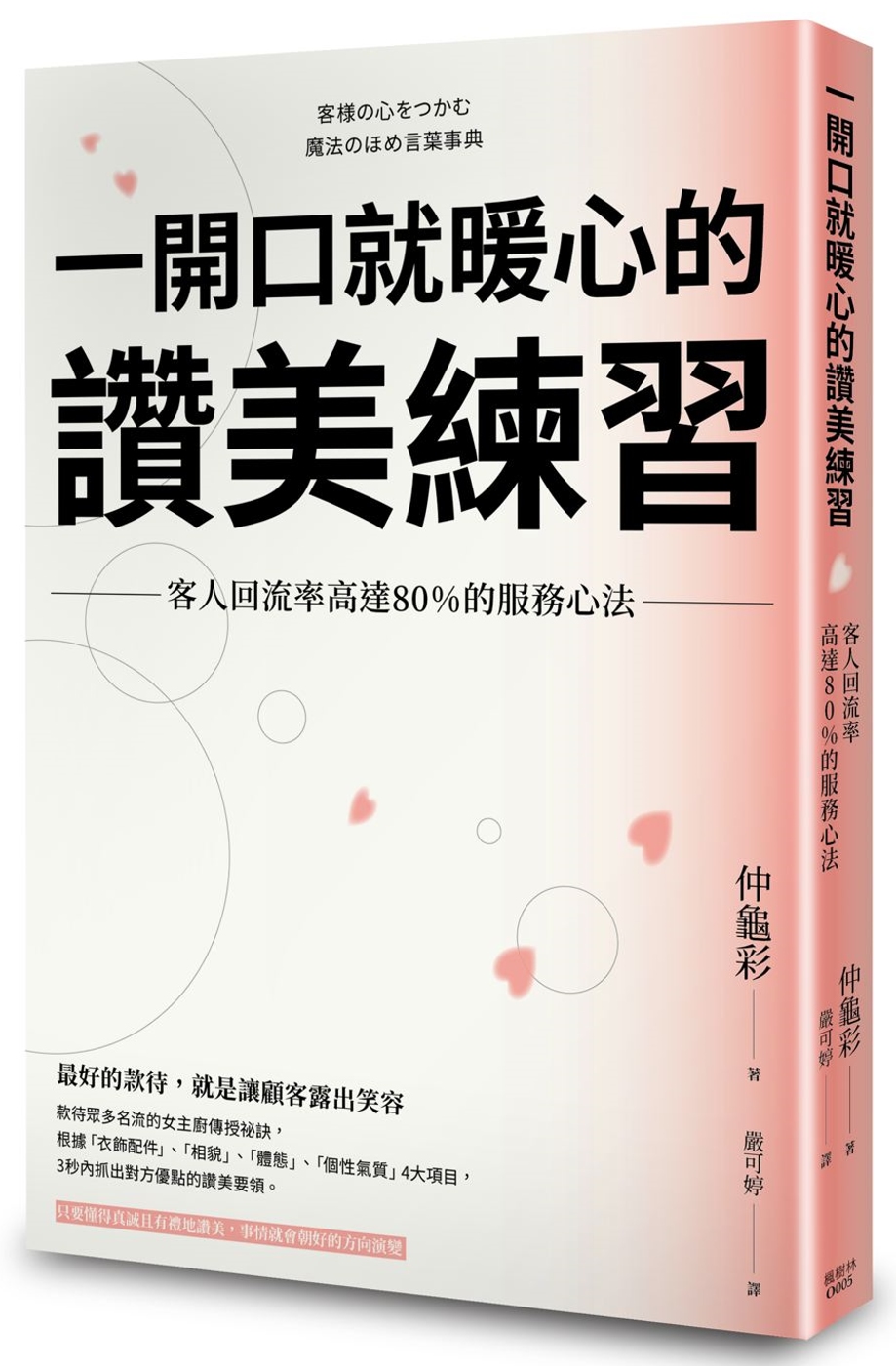 一開口就暖心的讚美練習:客人回流率...
一開口就暖心的讚美練習:客人回流率... 乖寶寶好習慣:不愛乾淨的小瑪
乖寶寶好習慣:不愛乾淨的小瑪 這樣也很好!大齡女子獨立宣言:丟掉...
這樣也很好!大齡女子獨立宣言:丟掉... 糖尿病有救了:完全逆轉!這樣做效果...
糖尿病有救了:完全逆轉!這樣做效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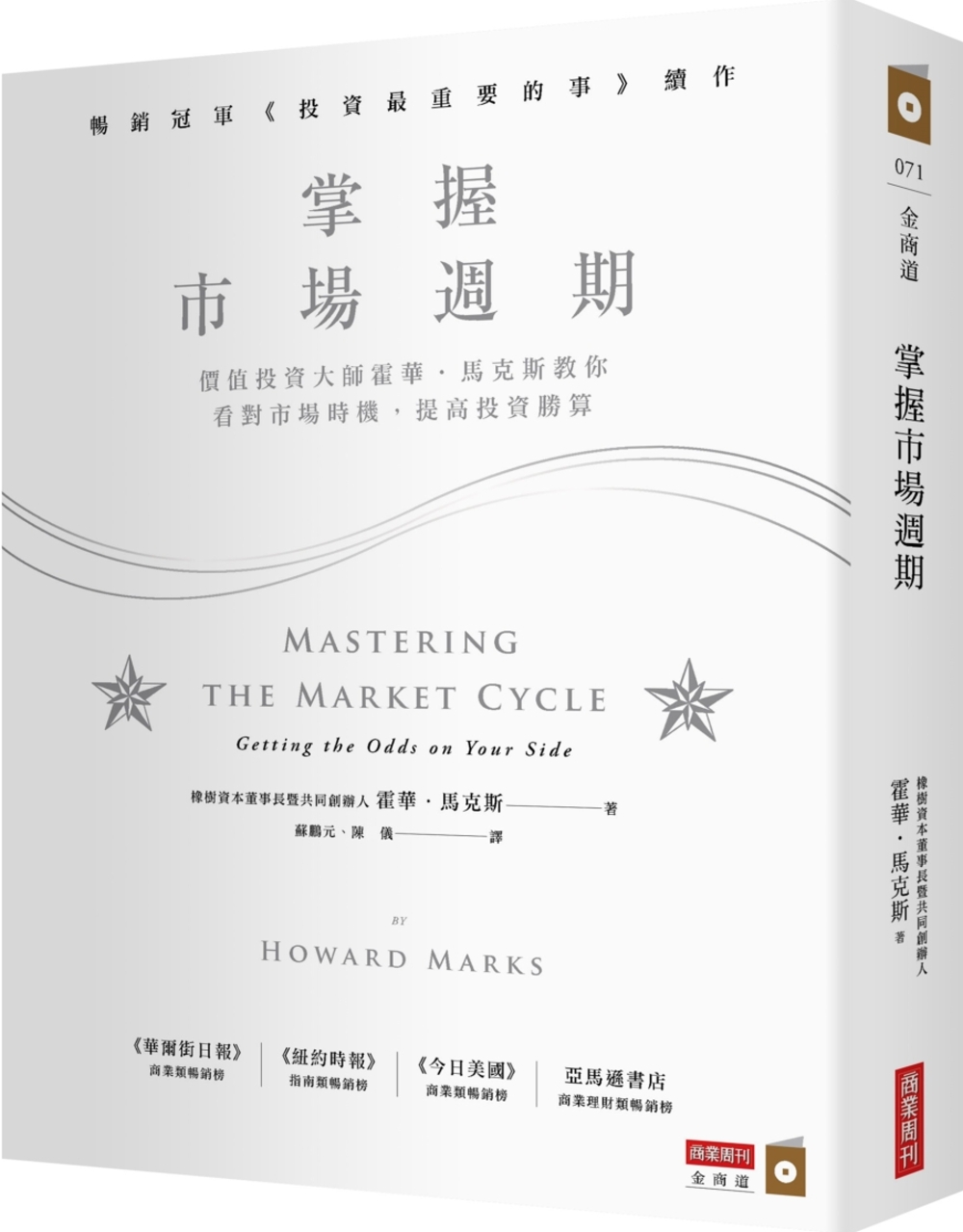 掌握市場週期:價值投資大師霍華.馬...
掌握市場週期:價值投資大師霍華.馬... 河圖洛書套書組 (河圖洛書新解 +...
河圖洛書套書組 (河圖洛書新解 +... 10倍速時代(新版)暢銷全球20年...
10倍速時代(新版)暢銷全球20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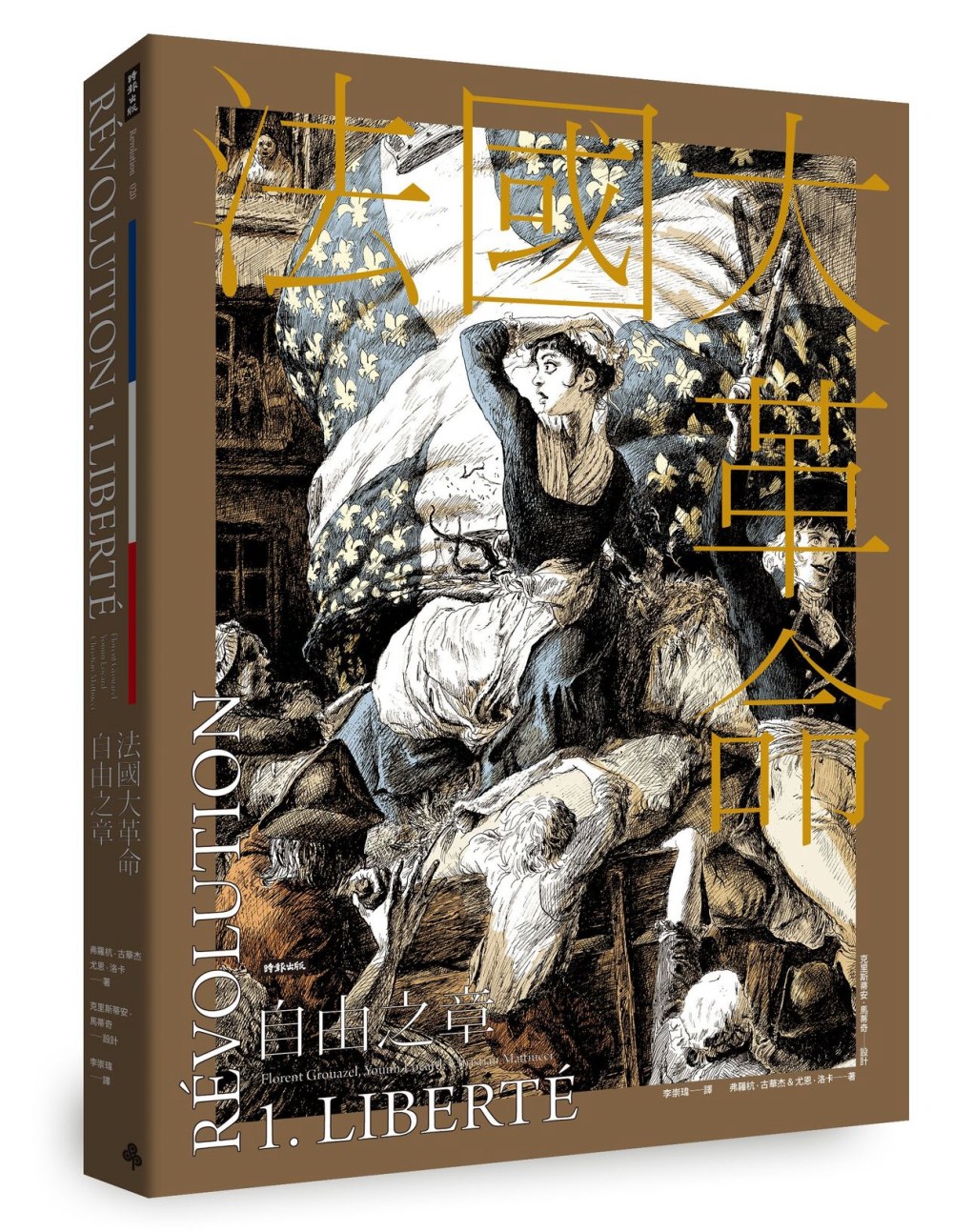 法國大革命:自由之章
法國大革命:自由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