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紀念選輯第4冊) | 被動收入的投資秘訣 - 2024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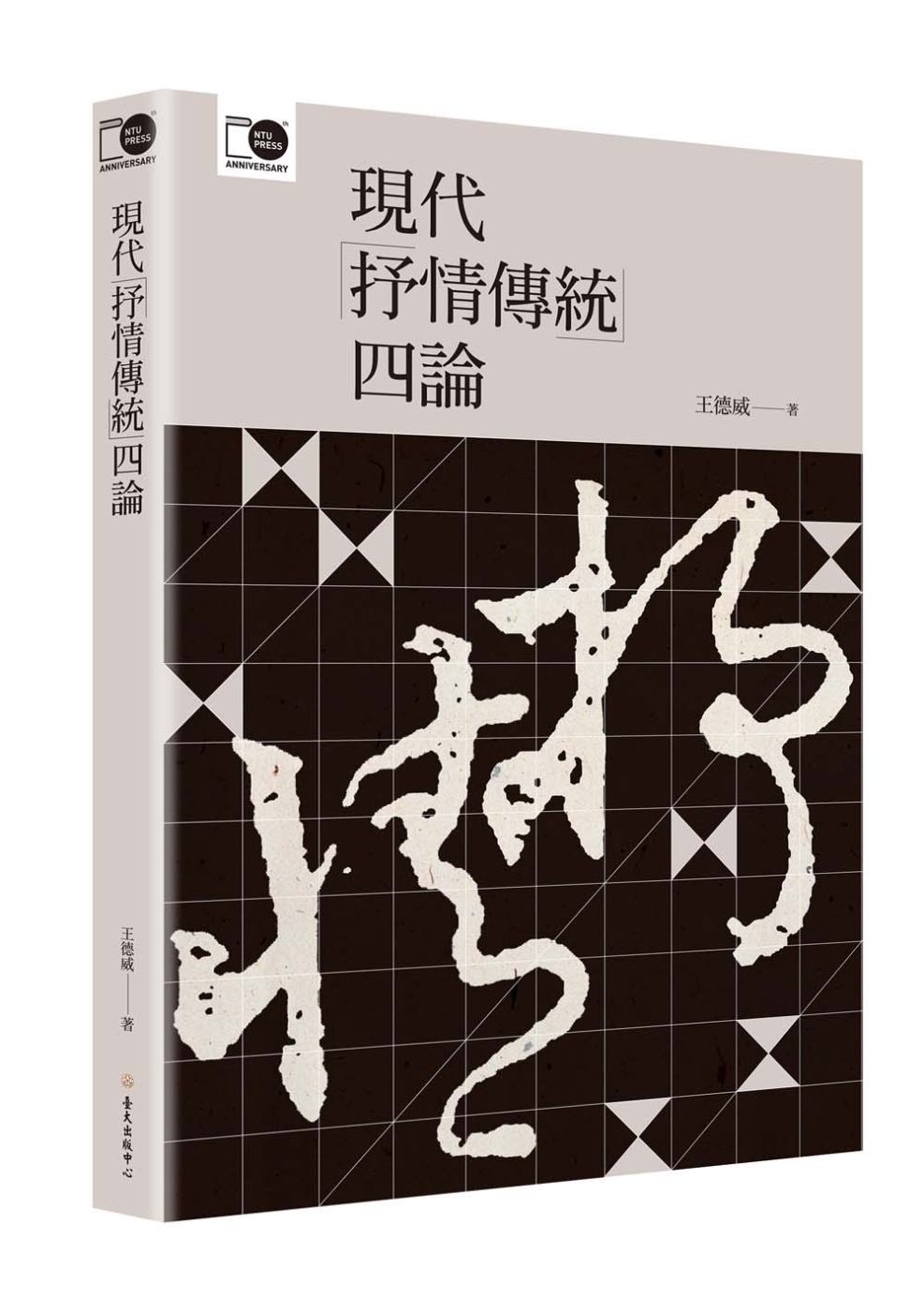
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大出版中心20週年紀念選輯第4冊)
「抒情」如何成就其「傳統」?又如何走向「現代」?
本書提出了極具突破性與啟發性的論述。
對於中國文學研究者而言,「抒情」是十分熟悉的語詞。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者開始參照西方文論反身重探傳統,並試圖以自身特質與西方文學對話,「中國抒情傳統」,正可視為此一過程中的「發明」。但究竟何謂「抒情」?「抒情」如何成為傳統?又如何走向「現代」?相關研究已累積豐富的成果,王德威教授所撰本書正是其中非常具有突破性與啟發性的論述。
本書以「現代性」觀點切入,討論中外學界對抒情話語的辯證與問難,洞見與不見;亦分別以江文也、臺靜農、胡蘭成為焦點,思考「抒情」的理念淵源、媒介形式、今昔對話、政治條件、個人抉擇,以及與臺灣研究的關聯性。全書強調抒情的「傳統」不應僅見諸文本和文論;在歷史經驗的脈絡裡,抒情的隱與顯更耐人回味。
★臺大中文系特聘教授梅家玲專文導讀
作者簡介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2004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第25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著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眾聲喧嘩:三〇與八〇年代的中國小說》、《閱讀當代小說:臺灣.大陸.香港.海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現代中國小說十講》、《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如此繁華:王德威自選集》、《後遺民寫作》、《一九四九: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等。
臺大出版中心二十週年紀念選輯總序/項潔
導讀 抒情的能量──閱讀《現代「抒情傳統」四論》/梅家玲
序/王德威
第一章 「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
一、前言
二、「有情」的歷史
三、「抒情」與「史詩」的辯證:比較文學的觀點
四、「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五、現代性下的「抒情傳統」
六、結語
第二章 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
一、前言
二、從「殖民的國際都會主義」到「想像的鄉愁」
三、孔樂的政治
四、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
五、尾聲
第三章 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
一、前言
二、史亡而後詩作
三、國家不幸書家幸
四、尾聲
第四章 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
一、前言
二、〈給青年〉――不要「吶喊」
三、「興」的詩學與政治
四、詩與欺騙
五、情之「誠」,情之「正」,情之「變」
六、尾聲
引用書目
導讀
抒情的能量──閱讀《現代「抒情傳統」四論》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對於中國文學研究者而言,「抒情」應是十分熟悉的語詞。早在屈原《九章.惜誦》寫下「發憤以抒情」開始,無論是詩詞歌賦,詩話文論,都不乏「抒情」一詞出現。但究竟何謂「抒情」?「抒情」如何成其為「傳統」?如何介入文學與藝術研究?又如何由「傳統」走向「現代」?近年來,已有不少海內外學者就這些論題進行研究,並積累出相當豐碩的成果。王德威教授的《現代「抒情傳統」四論》,正是其中相當具有突破性與啟發性的論述。對它的閱讀,至少可以從三個面向來把握:一是中西文學對話所帶出的「迴映」觀,二是「抒情」本身所內蘊的「流注」特質;三是現代性的批判觀點。
近世以來,從西學東漸到中體西用;從啟蒙自強到民族國家意識萌興,多方面地促成了中國的現代轉型,「文學」當然不能自外於此。無論是學科建立、知識框架形構抑是書寫實踐,大抵都在中外文化相互激盪之中逐步開展。中國文學研究者一方面參照西方文論反身重探傳統,另一方面,也試圖以自身特質與西方文學不斷對話,以期為「中國文學」尋求定位。而「中國抒情傳統」,正可視為此一過程中的「發明」。
就語源語義考掘,「發憤以抒情」的「抒」字或作「杼」,或作「舒」或「紓」。「舒」或「紓」,大抵解作宣泄、流注;「杼」則具有「梳理」之義。因此,「抒情」一詞,每每意謂原本內蘊於個人主體的「情」,基於某種原因往身外流注,而它又必得歷經作者將其「形式化」的過程。放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脈絡中勘察,詩賦以情志為本質,雖是長久以來普遍的共識,但「抒情傳統」一詞的出現,卻是現代產物,其間所關涉的,實則是一個「中西比較文學」的交涉過程:一九七一年,旅美學者陳世驤受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之邀,在「比較文學」小組發表〈論中國抒情傳統〉一文,明確指出:「中國文學傳統從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抒情傳統」。――而這正是「抒情傳統」一詞最初的來源。
陳世驤之說,明顯是基於中西「文學傳統」的相互參照:相對於歐洲文學中源遠流長的「史詩」與「戲劇」,中國文學固不著力於此,因為它的「榮耀別有所在」,那就是「抒情詩」。然而,中國古典文學中素無「抒情詩」之體類,「抒情詩」(lyric),以及因之而衍生出的「抒情性」(lyricality)、「抒情精神」(lyricism)等語詞,同樣是中西文學交涉協商的產物。其中,西方的「lyric」源出於與樂器相關的「歌」,其音樂之流動感在轉為文字書寫品之後,往往被詮釋為情感的流動。而也就在這一層面上,它不僅與中國「抒情」語義中的「流注」說有所匯通,並且使得「抒情精神」與「抒情傳統」之所涵蓋,並不局限於「詩」之體類,而可以轉化為「詩性精神」,進而流注、延擴至其他的藝術文化。爾後高友工教授論述〈中國文化史中的抒情傳統〉,所言不僅止於文學,更擴及音樂、書法、繪畫等不同藝術門類,即應著眼於此。
另一方面,「抒情」一詞既源於楚騷之「發憤以抒情」,這就使得作為中國文學傳統的「抒情」論述,從一開始就內蘊著重重的憂患意識與離散經驗。它形諸個人的詠物言志,其底蘊實出自對時局政治的回應。(個人的)「詩」與(群體的)「史」,從來就互為表裡。唐代「詩史」觀念出現,所謂「觸事興詠,猶所鍾情」,更點明抒情與歷史之間的綿密關聯。千百年來,小自個人遭逢,大至時代命運、歷史興亡,種種憂思憤悶,莫不經由「抒情」之詩性流注,形諸文學,并及各類藝術。然而,隨著時光推移,近代以來,文學的書寫體式,早已歷經了從文言到白話的轉折;傳統的藝術文化,也經由不斷的中外互動,展開不同面向的現代轉型。處身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不免要問:抒情的「傳統」是否仍然綿延於今?它是否足以體現駁雜萬變的現代經驗?而「抒情」除了作為經驗形式、文類風格或是政治姿態之外,我們是否還能將它視為「現代」的批評概念與介面,去開展其間思辨與批判的能量?
顯然,這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卻正是《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一書的用心所在。近年學界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曾因引進「抒情傳統」之論述框架而精彩紛陳;但所論一則多集中於文學,再則並不及於現代;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則又多局限於五四以來「革命」、「啟蒙」的論述框架,視「抒情」為小道,不曾將其納入觀照視野。此一現象,意謂著文學之「現代」與「古典」若有鴻溝在焉,「抒情」與「革命」似不兼容,若非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學養及識見,匯通誠屬不易。王德威教授臺大外文系畢業後,隨即赴美獲得比較文學研究博士。他的學術研究以五四之後的中國現代小說為起點,進而逐步開展。多年來,不但在時代上前溯晚清,體類上更跨越文學,旁及音樂書法電影等藝術,並同時關注其間的歷史與政治論題。他在中西比較文學方面的學術積累、由現代上溯古典的研究取徑,以及個人於歷史政治論題的關懷,都使《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具備了得以就前述提問進行層層思辨的可能。
《四論》凡四章,以〈「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開篇,繼之論江文也的音樂、臺靜農的書法,以及胡蘭成的詩學與政治,做法上,乃是以二十世紀中期的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為切入點,展開「抒情傳統」與「文學現代性」之間的論辨。首先,作為全書導論的〈「有情」的歷史〉,以沈從文、陳世驤與捷克漢學家普實克為座標,深入處理三個最根本的問題:一是傳統與現代能否匯通?它涉及了中國文學之現代性追求過程中,「抒情傳統」是否仍然賡續及其產生的語境如何等議題。二是中西文學如何對話?我們能否循由比較文學的脈絡,探勘「抒情」與「史詩」的辯證,並將中國與西方之於「抒情」的論述迴映互參,檢視各自的洞見與不見?三是回到現代文學研究,探問「抒情傳統」將可以為此一領域開發出哪些新興的研究論題?
循此,該章指出,在革命啟蒙之外,「抒情」實為中國文學之現代性主體建構的另一重要面向。二十世紀戰亂頻仍,無論是國家民族至上的呼聲,抑是階級群眾掛帥的籲求,都使得文學儼然進入唯群體是尚的「史詩」時代。但即或如此,「抒情」聲音依然不絕如縷。甚至於,正因為此一政治裂變、時局動盪的「現代經驗」有別於既往,由有心人所召喚出的「抒情傳統」,便也在上承「發憤以抒情」之固有內涵的同時,被賦予了現代精神。〈「有情」的歷史〉以陳世驤和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抒情與史詩傾向的研究為座標,梳理了二十世紀前期到中期以來,西方學者們在「詩」與「史」之間所作的種種調適或辯證;同時,也檢視自晚清以降,中國學者由「情」而轉向「抒情」論述的旨趣走向。經由比較文學的視野,我們看到自魯迅、王國維以迄於郭沫若、朱光潛、朱自清、聞一多、梁宗岱、沈從文等,如何與西方浪漫主義的「抒情」論進行對話。中西迴映參照之餘,〈「有情」的歷史〉於是進一步為現代文學研究提出三項有待深化的研究課題,分別是:「興與怨」、「情與物」、「史與詩」。
事實上,這三項論題原都是中國古典文論關切的重點,如今轉置於中西文學對話的現代語境,其意涵當然也隨之因革變化。因此,其後關於江文也、臺靜農與胡蘭成之文學藝術的抒情現代性討論,便是以具體個案為例,既分就音樂、書法、詩學政治之抒情現代性問題各別深論,也就此三項課題進行闡析,並各有側重。
其中,〈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結合了江文也的音樂作品、詩歌和理論文章,論證他的現代感性如何突顯了殖民性、民族性與國際都會性的混淆特質;他在戰爭期對於儒家音樂及樂論的鑽研,如何為中國文化本體論與日本大東亞論之間帶來對話,以及個人之「抒情」視野如何因為「歷史」機遇而同時受到激發與局限。江文也的個案,具體落實了「史與詩」的辯證:「史」,在此並不僅止於「歷史」之現實,也不同於傳統詩論中的「詩史」,而是源自於西方文論的「史詩性」,也就是如普實克所指稱的,集體的政治呼嘯;「詩」,則為個人的詩意表達。普實克在觀察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進程時,曾以「抒情性」相對於「史詩性」來予以界定;江文也的一生,恰恰見證了普實克對於中國現代性這兩種聲音母題的觀察。而另一方面,當然也初步回應了前述的問題:抒情的「傳統」不但仍然綿延於今,並且流注於音聲樂曲,適以體現出駁雜萬變的現代經驗。
繼〈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之後,〈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藉由臺靜農的文學書寫與書法美學,闡明三項議題:現代文學與書寫形式的辯證;現代書法與政治、文化「南渡」論述的對話,以及書法與「喪亂」詩學無聲勝有聲的關聯。值得注意的是,其小說與舊體詩的寫作,固然是古典詩學之「興與怨」的現代實踐;而隱現於其書法翰墨之中的,其實是對於「情與物」之課題的現代闡發。
「緣情感物」曾是魏晉以來文論的重心,無論是陸機的「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劉勰的「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抑是鍾嶸的「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在在都揭示情物之交感,是為文學書寫的內在驅力,這也就是所謂的「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只是其時所「感」之「物」,莫不來自於四時推移、自然物色,並不及於人為的文物藝品。然而先前沈從文之寄情於古代文物研究,已為我們演示了抒情現代性的另一向度:他的「抽象的抒情」,其實兼括了「情」與「物質文明」的交會交感。臺靜農早年曾參與圓臺印社,藉治印摩挲古代文字形貌;抗戰時期「每感鬱結,意不能靜,惟弄毫墨以自排遣」。至此,「情」與「物」之於臺靜農,遂不僅止於觀摩先人碑帖之後的「應物斯感」,而是進一步託情於物,經由筆墨紙硯,揮灑出抒情的書藝――亦即進一步參與了「物」的生成創製,並從中銘記一個時代的喪亂、創傷,與失落。「情與物」的課題,於是在現代情境中翻轉開展,產生了別開生面的交融共感,相生相成。
最後,〈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與戰後的詩學政治〉,則是以胡蘭成在戰爭與戰後期間的作品與行止,探討其詩學政治,闡明「詩」與「史」的另一現代詮解,及其與「興」義之間的彼此生成關係。這是「現代抒情傳統」最特殊的一章,原因是胡蘭成對於「情」的論述及其言行實踐,在在充滿了機巧的悖論。他在戰爭期間以充滿抒情風格的文字為自己的背叛、通敵與濫情自圓其說,動搖了「抒情」一向作為「誠於中形於外」的表述形式,形成一種文字的叛/變術;他高度推崇「情」的意義,以為「革命」是出於「情」的驅動,看似匯通了史與詩、集體與個人,但真正的革命與真正的情,總是內蘊了對於既有體制的反叛,這似乎又為他種種的「背叛」行徑找到合理化的理論依據,並因之形塑出中國現代性中的另一新型主體:「蕩子」。更有甚者,他發展抒情傳統中「興」的「上舉歡舞」之義,以之詳參歷史,統攝宇宙,並且通過它,將民間的迎神賽會與「革命」及群眾暴力相連結,推衍出「中國的革命是興」、「中國的革命原來是迎神賽會,……有喜氣」。於是,「興」非但是無中生有的創造力來源,也是民間歡慶的如花佳節,更成為革命暴力的內在源頭。至此,胡蘭成為「抒情」論述所做出的種種演繹,便也不僅是以他的「善變」,成為抒情傳統的現代「變」調,並且極其奇詭地呼應了「現代性」的核心要義:過渡、短暫、偶然。
由沈從文、陳世驤、普實克,以迄於胡蘭成,《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已為「抒情傳統」與「現代性」開展出多面向的論辯。它以比較文學的視野,進行中西文學傳統的迴映參照,也以「抒情」所內蘊的「流注」特質,匯通了古典與現代、文學與藝術文化,在在演示出「抒情」作為現代學術研究之介面的豐沛能量。但除此之外,本書另一重要意義,應是揭示了現代性的「批判」精神:經由不斷詰問並辯證「抒情」的可能與不可能,去深化思辨的向度。一開始,〈有情的歷史〉便指出:二十世紀以降,是一個崇尚「史詩」的時代,在不可能抒情、難以抒情的時候,我們要如何談論它?「抒情」如何與現代經驗中的「革命」、「戰爭」、「暴力」、「殖民」、「叛變」對話?又如何從中開展它的動能?因此,無論是江文也、臺靜農,抑是胡蘭成,各篇所論述的「抒情」,都不唯是「傳統」的綿延,而是以其各人的現代體驗,回應並豐富了「抒情」的內涵。就學術研究而言,此一思路所揭示的問題意識及其論證過程,對於學界的啟發性,將可能更甚於「現代抒情傳統」本身的研究。
王德威教授對於「抒情傳統」的研究涵蓋深廣,本書所收錄者,只是其中與「臺灣」相關的部分而已。2015年初,他的英文專著The Lyrical in Epic Time: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所探討的論題,除本書的「四論」之外,還包括沈從文的三次啟悟、馮至與何其芳的詩歌、林風眠的繪畫、費穆的電影藝術等。2011年,王教授將《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先行交付臺大出版中心,作為《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叢書》的啟動之作,除卻它的「臺灣研究」面向之外,其實另有深意:1958年陳世驤教授受邀在臺大文學院進行四次學術演講,由此開啟了臺灣學者對於「抒情傳統」的關注;1978年高友工教授自美返臺於臺大客座講學,又從不同進路,深化、擴大了「抒情傳統」對學界的影響。爾後,中國古典文學之「抒情傳統」的研究者,多與臺大深有淵源。可以說,臺灣的「抒情傳統」研究,原就是發軔於臺大。而今,《現代「抒情傳統」四論》將研究的論域擴展至現代,既是「抒情傳統」之研究論題的現代推展,也再次凸顯此一研究與臺大,乃至臺灣學界的在地淵源;它向前輩學者致敬,也召喚著新一代學者持續就此深耕細耘,日新又新。
2016年1月
作者序
王德威
「抒情」在現代文論裏是一個常被忽視的文學觀念。一般看法多以抒情者,小道也。作為一種詩歌或敘事修辭模式,抒情不外輕吟淺唱;作為一種情感符號,抒情無非感事傷時。五四以來中國的文學論述以啟蒙、革命是尚,一九四九年之後,宏大敘事更主導一切。在史詩般的國族號召下,抒情顯得如此個人主義、小資情懷,自然無足輕重。
然而只要我們回顧中國文學的流變,就會理解從《詩經》、《楚辭》以來,抒情一直是文學想像和實踐裏的重要課題之一。《楚辭.九章》〈惜誦〉有謂「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時至二十世紀初魯迅寫〈文化偏至論〉,則稱「鶩外者漸轉而趣內,淵思冥想之風作,自省抒情之意蘇,去現實物質與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靈之域。」這裏抒情的用法和喻義當然極為不同,但惟其如此,才更顯現這一詞彙的活力豐富,千百年來未嘗或已。
抒情的「情」字帶出中國古典和現代文學對主體的特殊觀照。從內爍到外緣,從官能到形上,從感物到感悟,從壯懷激烈到纏綿悱惻,情為何物一直觸動作家的文思;情與志、情與性、情與理、情與不情等觀念的辯證則豐富了文學論述。
而「抒」情的抒字,不但有抒發、解散的含義,也可與傳統「杼」字互訓,因而帶出編織、合成的意思。這說明「抒情」既有興發自然的嚮往,也有形式勞作的訴求。一收一放之間,文學動人的力量於焉而起。後之來者談中國主體情性,如果只能在佛洛伊德加拉崗,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或情感論(affect theory)這些西學中打轉,未免是買櫝還珠之舉。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對抒情的理解深受西方浪漫、現代主義的影響。拜倫和雪萊,或波特萊爾和艾略特成為新的靈感對象。然而傳統資源的傳承不絕如縷。魯迅、王國維等人不論,魯迅眼中「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馮至同時接受杜甫和理爾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影響;何其芳的抒情追求從唯美的瓦雷里(Paul Valéry)轉到唯物的馬雅克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卻總不能或忘晚唐的溫李;瞿秋白就義前想到的不是馬克思,而是《詩經》名句,「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撇開人云亦云的偏見,我們乃知現代文人學者—甚至革命者—折衝在不同的抒情淵源、條件和效果之間,早已為這一文學觀念開發出更多對話空間。
一九七一年,旅美的陳世驤先生(1912-1971)發表〈中國抒情傳統〉,指出中國文學的精華無他,就是抒情傳統。陳認為中國早期文學「詩意創造衝動的流露,其敏感的意味,從本源、性格、和含蘊上看來都是抒情的」,即使明清的小說戲曲也難以自外這一傳統。陳先生的立論對海外古典中國學界帶來深遠影響,至今臺、港、新加坡等地相與呼應者大有人在。美國的高友工教授日後另闢蹊徑,談論「抒情美典」,也間接延續了「抒情傳統」的魅力。
陳先生的文章言簡意賅,其實頗有可以大加發揮的餘地。他談的是抒情「傳統」,卻深深立足在現代語境裏。三〇年代陳負笈北大外語系,與京派文人往還,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和理論知之甚詳。一九四一年陳赴美國,開始轉向古典文學研究。而去國三十年後,在中國動盪不安的年月裏,他潛心抒情傳統,更不能不讓我們聯想蘊積在他心中的塊壘。
承續以上觀察,這本論集是我個人對抒情傳統與現代性所作的初步研究。收錄的四篇文章中,〈「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縱論多年中外學界對抒情話語的辯證與問難,洞見與不見,並提出一己的見解。另外三篇,〈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國家不幸書家幸〉、〈抒情與背叛〉則分別以三位現代文學史與文化史人物――江文也(1910-1983)、臺靜農(1902-1990)、胡蘭成(1906-1981)──為焦點,思考「抒情」的理念淵源、媒介形式、今昔對話、政治條件、個人抉擇。我認為抒情的「傳統」不應僅見諸文本和文論而已,也應落實在人間煙火之中。惟有在歷史經驗的脈絡裏,抒情的隱與顯才更加耐人回味。
第一章〈「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
本章提議在革命、啟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國文學現代性──尤其是現代主體建構──的又一面向。一般論述對「抒情」早有成見,或視為無關宏旨的遐想,或歸諸主觀情緒的耽溺;左翼傳統裏,「抒情」更帶出唯心走資等聯想。論者對「抒情」的輕視固然顯示對國族、政教大敘述不敢須臾稍離,也同時暴露一己的無知:他們多半仍不脫簡化了的西方浪漫主義說法,外加晚明「情教」論以來的泛泛之辭。但誠如學者已指出,西方定義下的「抒情」(lyricism)與極端個人主義掛鉤,其實是晚近的、浪漫主義的表徵一端而已。而將問題放回中國文學傳統的語境,我們更可理解「抒情」一義來源既廣,而且和史傳的關係相衍相生,也因此成就了中國現代主體的多重面貌。
本章以二十世紀中期為切入點,試圖為中國抒情傳統與現代性的對話作進一步的描述。一般皆謂二十世紀中期是個「史詩」的時代,但恰恰是在這樣的時代裏,少數有心人反其道而行,召喚「抒情傳統」,才顯得意義非凡。這一召喚的本身已經饒富政治意義。更重要的,它顯現了「抒情」作為一種文類,一種「情感結構」,一種史觀的嚮往,充滿了辯證的潛力。
本章的討論將以沈從文(1902-1988)、陳世驤,以及捷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為坐標。這三人立場、國籍不同,發言的位置有異,但他們不約而同,都企圖在現代語境裏重新認識抒情傳統。他們的洞見讓我們理解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問題不能由革命、啟蒙的話語一以蔽之;而他們的不見顯示抒情「傳統」與現代性交會下,有待繼續思辨釐清的盲點。而本文建議陳、沈、普的論述為我們示範了三項課題:「興與怨」、「情與物」、「詩與史」。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描述陳世驤、沈從文、普實克論「抒情傳統」的語境;第二部分從比較文學的脈絡討論普實克、陳世驤的貢獻,以及二者與世紀中期西方其他抒情學說的關係;第三部分檢討晚清、五四以來,傳統定義的「抒情」與西方浪漫主義影響下的抒情論述間的種種對話;第四部分回到陳、沈、普三人的論述,並思考「抒情傳統」可以為中國現代文學開發出的新課題。
第二章〈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江文也的音樂與詩歌〉
江文也是二十世紀最有原創力的臺灣作曲家兼詩人。江文也早年赴日,深受西方現代派音樂的洗禮,一九三六年以管弦樂曲《臺灣舞曲》在柏林奧林匹克音樂比賽中獲獎。一九三八年江文也回到北平任教,致力重譜中國雅樂。影響他的關鍵人物是亞歷山大.齊爾品(Alexander Tcherepnin, 1899-1977),一位熱切崇尚東方音樂的俄國作曲家。江文也與中國音樂的邂逅或許給我們留下一個極其浪漫的印象。然而只要仔細回顧他的歷程,我們就會理解其中的曲折。他的前衛、跨國姿態總也不能擺脫殖民地臺灣之子的陰影;他所醉心的西方現代主義必須經由日本的中介才能有所得;而讓他生死相許的中國情懷其實來自一位俄國導師的啟發。江文也在不同文化和地緣政治的板塊間來回遊走,代表了一代臺灣藝術家如何努力調整自己的身分,回應從殖民主義到帝國主義,從民族主義到國際都會主義(cosmopolitanism)等各種挑戰。
當江文也一九三八年抵達北京時,中國已經陷入抗日戰爭的漩渦中。然而江文也的藝術生涯卻在淪陷的北京蓬勃發展,並在四〇年代初達到高潮。他試圖以交響樂《孔廟大晟樂章》(1939)和中日文的詩歌重新定義中國音樂和文字的精髓—儒家禮樂精神。他的音樂和詩歌融合了過去與現在,在「想像的鄉愁」形式下,他進行著大膽創新。
已故的捷克漢學家普實克在觀察現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進程時,曾以「抒情性」相對於「史詩性」──或個人的詩意表達相對於集體的政治呼嘯──來界定。江文也一生見證了普實克對中國現代性這兩種聲音母題的觀察;它顯示了現代中國對「新聲」的追求如何總落入或緘默、或爭辯、或陰鬱、或狂熱的循環。
本章將討論江文也在他生涯的轉折點上,如何對「聲音」的現代性作出選擇,以及所必須承受的美學與政治後果。準此,本章以江文也的音樂作品、詩作和理論文章為例證,探問以下的議題:他的現代感性如何凸顯了殖民性、民族性與國際都會性的混淆特質;他在戰爭時代對儒家音樂和樂論的鑽研如何為中國文化本體論與日本大東亞主義間,帶來了不可思議的對話;以及更重要的,歷史的機遇如何激發也局限了江文也的抒情視野。
第三章〈國家不幸書家幸──臺靜農的書法與文學〉
五四一輩的知識分子文人裏,臺靜農先生的經歷可謂傳奇。一九二〇年代臺靜農在北京嶄露頭角,以鄉土文學和革命立場見知文壇,深受魯迅器重。臺並因為左翼關聯,三次被捕入獄。抗戰期間,臺避難四川,雖然仍寫作古典詩歌和歷史小說,卻另在書法中發現寄託。一九四六年臺因緣際會,赴臺灣任教,從此放棄文學,專攻書法,竟因此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書法大家之一。
本章討論臺靜農在二十世紀四、五〇年代的蛻變。面對家國動亂,臺在無所逃遁之際,寄情書寫。然而他不再追求文學的微言大義,轉而呈現文字的「表面文章」。臺靜農早年雖享有文名,但他的書法才真正顯現其人的性情。而他的書法更必須置於千百年來世變之際,文人「南渡」的歷史創傷和審美實踐上,才更見深意。
二十世紀中期臺靜農的「書法轉向」或出於政治考量,或出於離散心境,歷來眾說紛紜。本章則認為臺靜農此時對歷史經驗和藝術呈現的觀照,因書法而有了重要轉折。書法未必是對傳統文人藝術的回歸,也可能是反思現代性得失的關鍵。現代文學的啟蒙、革命號召有時而窮;是「書寫」傳統形式的千變萬化,反而激發層層有關歷史、家國,以及身分認同的空間想像。準此,本章將就以下三項議題深入發揮。一:現代文學與書寫形式的辯證;二:現代書法與政治、文化「南渡」論述的對話;三:書法與「喪亂」詩學無聲勝有聲的關聯。
第四章〈抒情與背叛──胡蘭成戰爭和戰後的詩學政治〉
胡蘭成是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史中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他在第二次中日戰爭期間與汪精衛政權的分合關係,和他與張愛玲(1920-1995)以及其他女性的浪漫情史,使他的形象一直充滿負面色彩。另一方面,他的文采見識,以及晚年對臺灣文學的影響,又使他成為一位傳奇人物。本章以胡蘭成戰爭和戰後期間(1939-1959)的作品和行止為重點,探討胡的詩學和政治、歷史觀點如何形成複雜的戰爭與文學論述。
本章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胡蘭成早期生平和戰爭期間的文字。胡自命為真正的革命家,他的思維脫離五四以來以西方國家主義、啟蒙精神、工具理性是尚的主流,相對的,他強調革命和「情」息息相關。但胡的「革命即抒情」觀已經透露法西斯主義「政治美學化」的傾向;而他假道日本的中國中心主義使他墮入東西二元論的另一極端。
第二部分以胡蘭成流亡日本後的作品《山河歲月》(1954)為中心,討論戰後胡的書寫方向。胡力求以「詩」注「史」,強調中國文明的發展惟日月山川、禮樂風景的轉換。此一轉換反映在政治上為井田制度的消長,反映在認識論上為「興」的美學的流變。胡強調「興」的表徵不僅及於禮樂風景,更包含「民間起兵」的力量:「惟中國的革命是興」。胡視中國現代史處處「驚險」皆化為「驚豔」,但無從擺脫其下的暴力和創傷。
第三部分討論胡蘭成的抒情詩學及其悖論。胡將抒情的「興」活學活用,使之成為縱觀天下,參詳歷史,甚至統攝宇宙萬物的法則。胡的學說誇張了中國抒情傳統最明媚的部分,也因而暴露其內蘊的危機:當抒情本體被無限放大,「歷史的不安」被架空,抒情總已滋生抒情的背叛。第四部分以胡蘭成的自傳《今生今世》(1959)為中心,討論胡蘭成抒情論的核心──情──的辯證。胡引用古典「蕩子」作為情的主體意象;他對情的思考和實踐可以表現在愛欲、政治及思想三方面。胡更賦予他的抒情論述一層哲學觀照;他與新儒家如唐君毅、徐復觀等的往還辯難俱見其人野心。
本書只是我進行中的研究部分成果而已,各章立論當然有未盡之處。唯一可以說明的是所論三位人物都與臺灣發生關聯,因此讓此書稍有前後呼應的脈絡。在此我要感謝引領我進入抒情傳統研究的諸位師友,尤其是柯慶明教授、張淑香教授、鄭毓瑜教授、陳國球教授等。陳國球教授兼治中西比較詩學;他的博學和洞見在在使我受益匪淺。我也要感謝臺灣大學臺文所所長梅家玲教授極力促成此書的出版,以及臺灣大學出版中心紀淑玲女士的悉心編輯。我期待各章論文得到方家的批評指正,作為繼續研究的動力。
2011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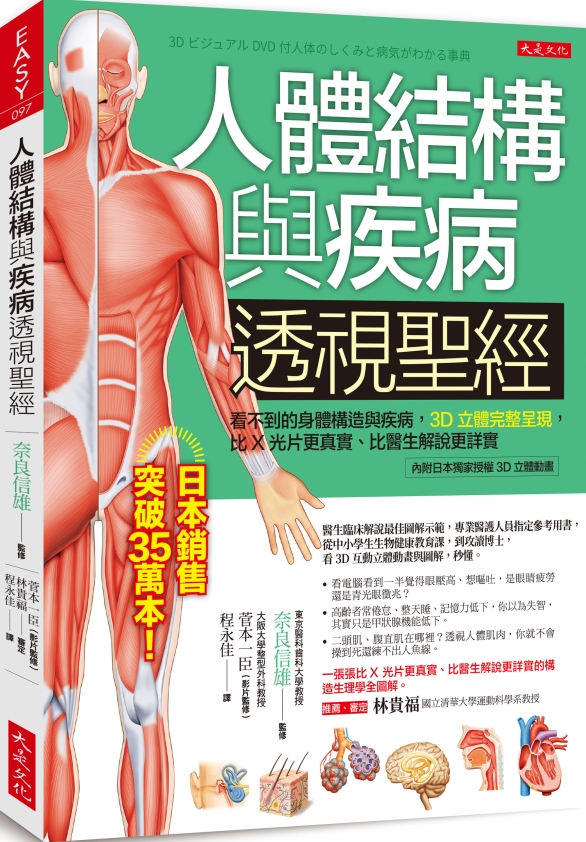 人體結構與疾病透視聖經:看不到的身...
人體結構與疾病透視聖經:看不到的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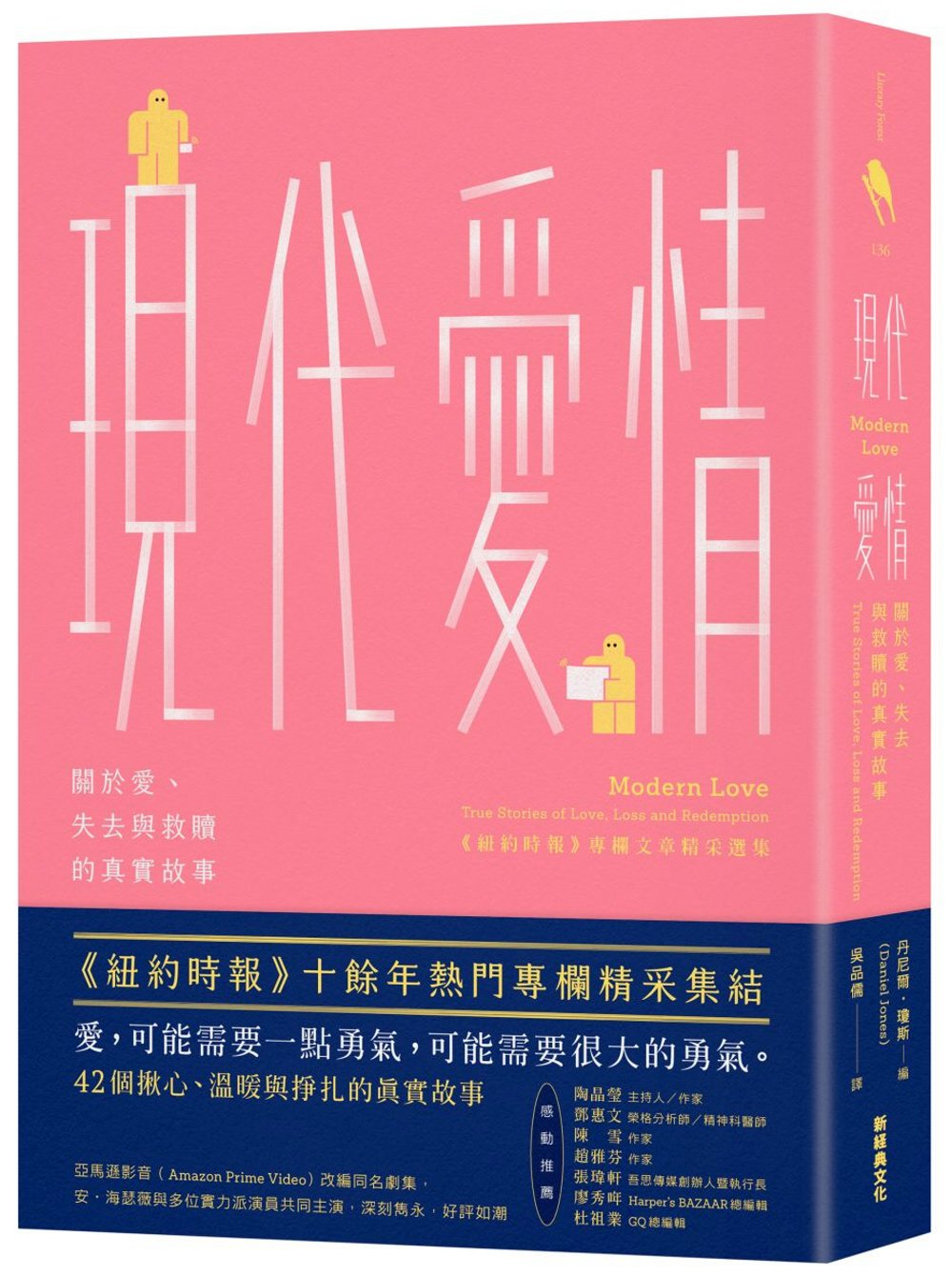 現代愛情:關於愛、失去與救贖的真實故事
現代愛情:關於愛、失去與救贖的真實故事 零歲開始蒙特梭利教育:從家庭落實的...
零歲開始蒙特梭利教育:從家庭落實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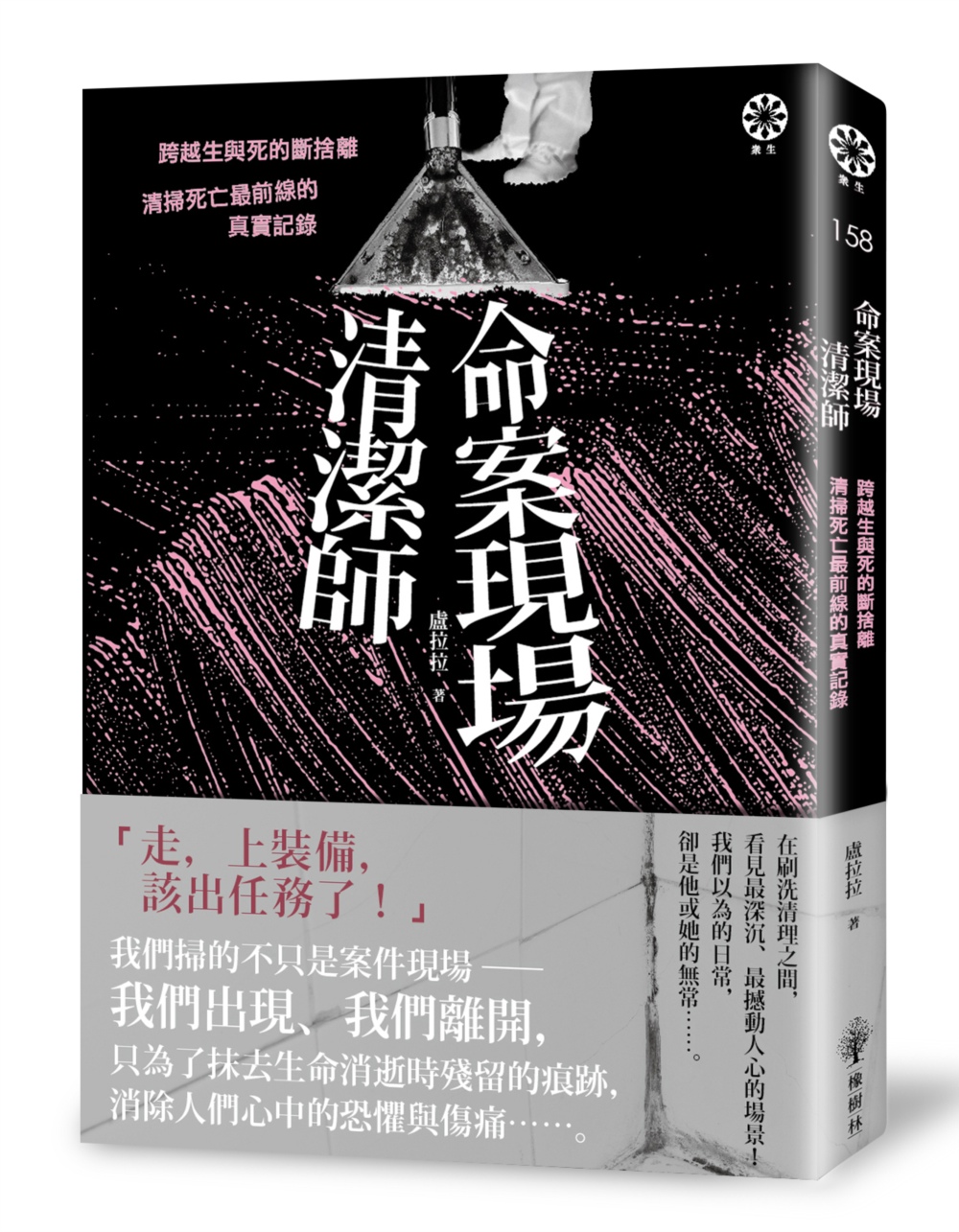 命案現場清潔師:跨越生與死的斷捨離...
命案現場清潔師:跨越生與死的斷捨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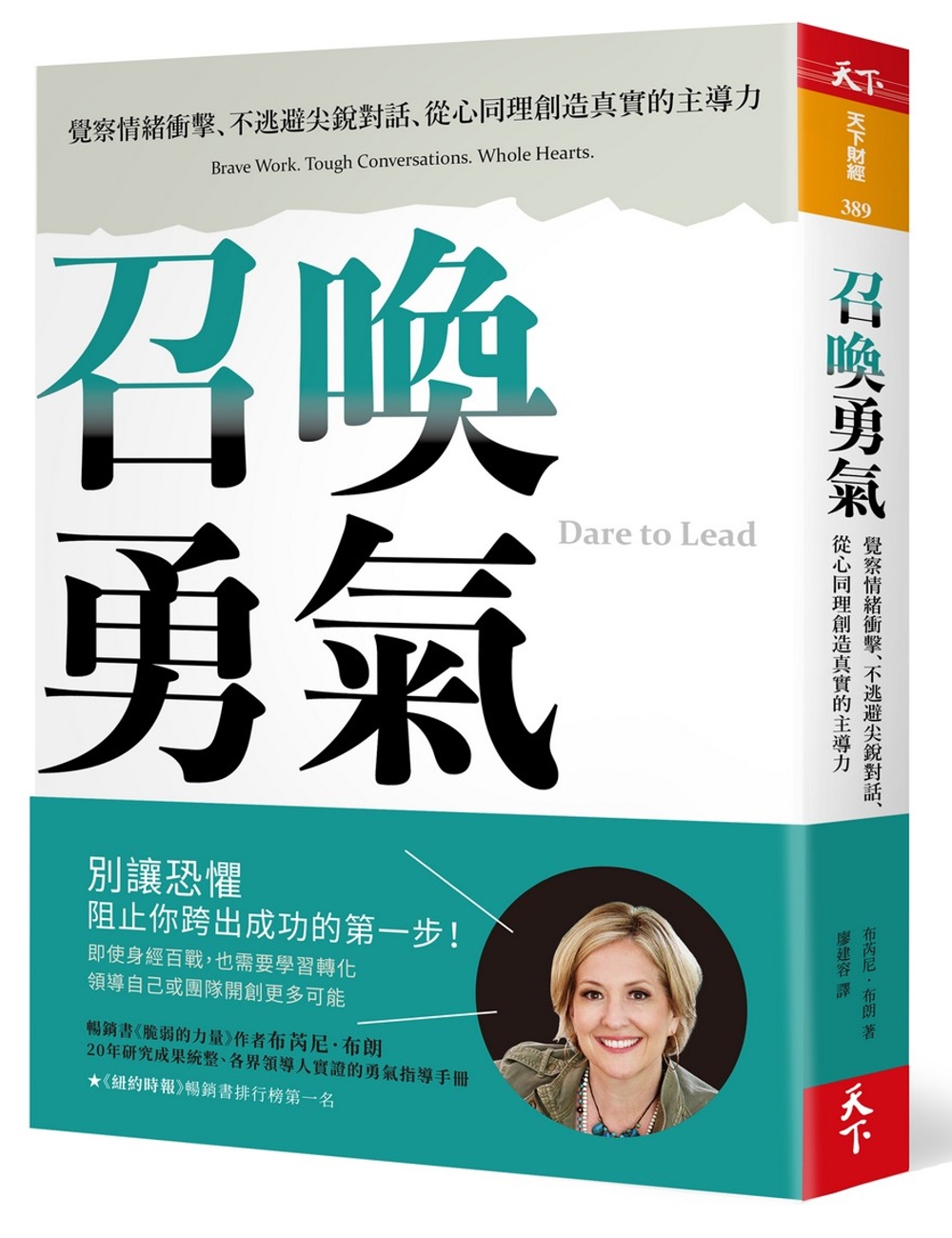 召喚勇氣:覺察情緒衝擊、不逃避尖銳...
召喚勇氣:覺察情緒衝擊、不逃避尖銳... 圖解女性心理學:女人不說、男人不懂...
圖解女性心理學:女人不說、男人不懂... 歸零,遇見真實:一位行腳僧,164...
歸零,遇見真實:一位行腳僧,164... 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
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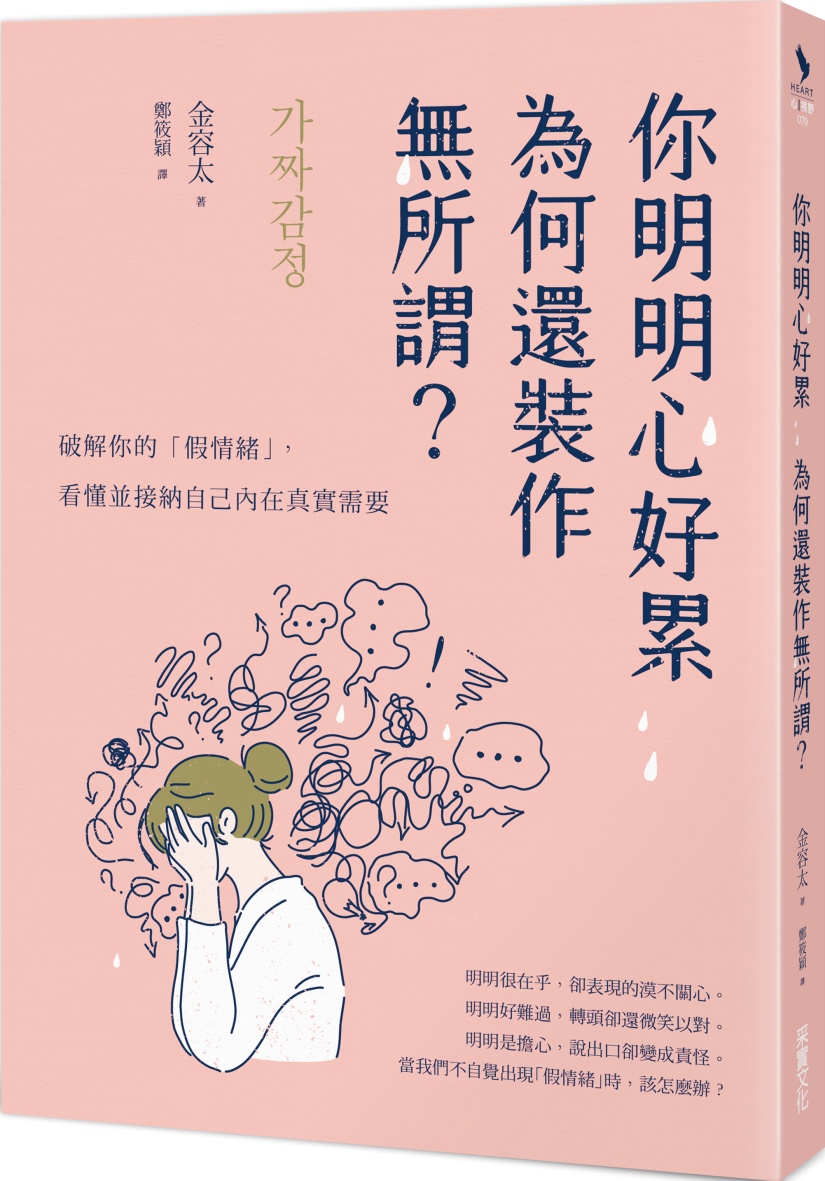 你明明心好累,為何還裝作無所謂?:...
你明明心好累,為何還裝作無所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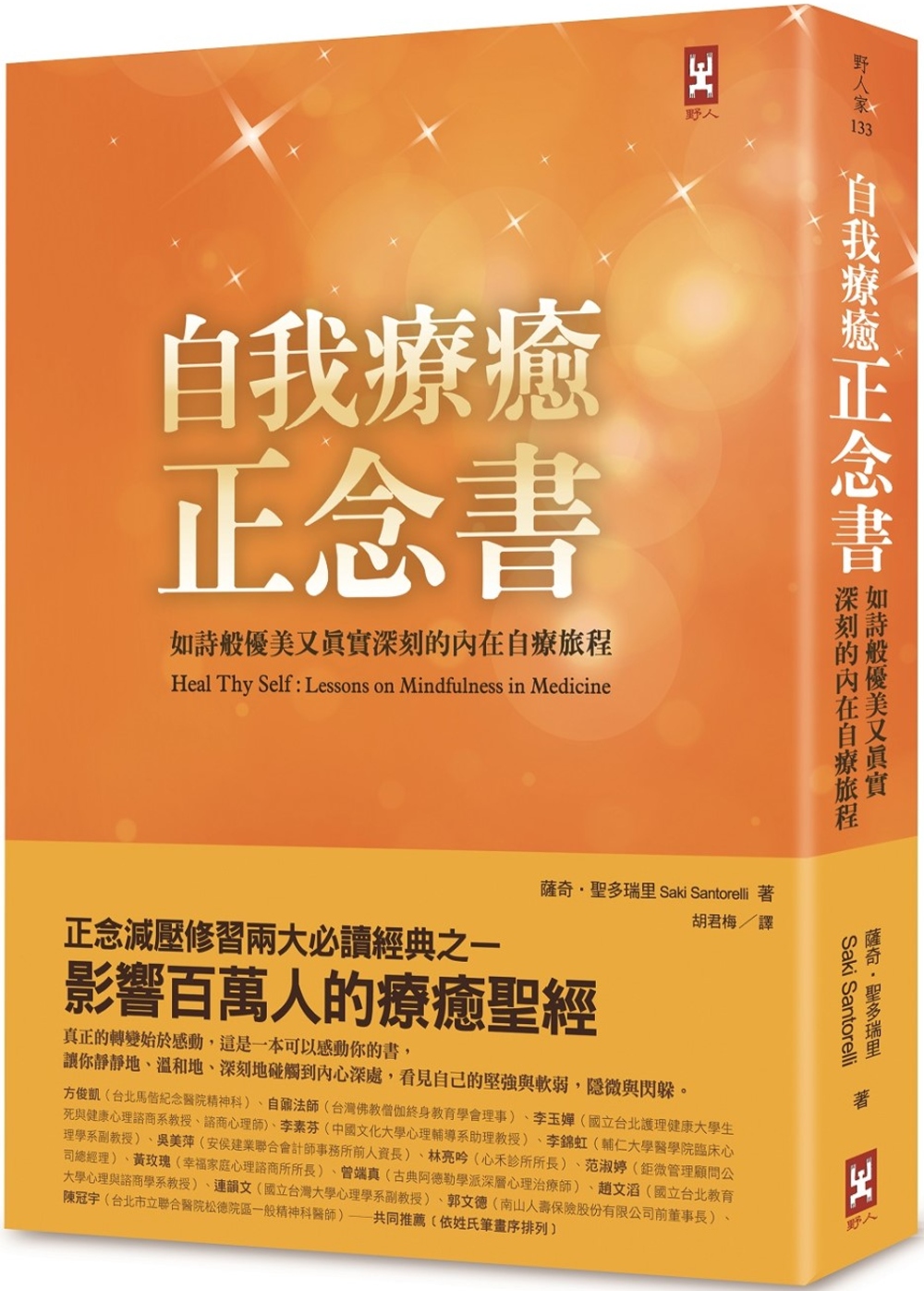 自我療癒正念書:如詩般優美又真實深...
自我療癒正念書:如詩般優美又真實深...